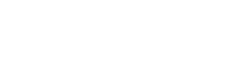肖鹰
草圣张旭的一生,犹如神龙不见首尾;它却又是极致的单纯简易,化约为“酒”与“书”两个字。
欧阳修主撰《新唐书》,其中《张旭传》开篇即如是:“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这篇传文仅157字,真是惜墨如金,但开篇这40字除“苏州吴人”外,全着墨于张旭酒事了。
然而我们知道,张旭最为后世所记的,是他开创的卓绝惊世的狂草艺术,他生前即享有“草圣”的殊荣。如果说东汉张芝使草书达于“精熟神妙”,东晋王羲之父子进而“韵媚婉转”(张怀瓘《书断》),那么,至唐代,张旭则将草书开拓到“逸轨神澄”的狂草境界(窦衆《述书赋》)。
后世名家评张旭,普遍集中于张旭草书的神奇变化,“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唐·韩愈),“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明·王世贞)。张旭的狂草将书法艺术的书写自由推向字与非字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正如他身体的沉醉放达,张旭对书写极限的挑战,犹如一出风起云涌的歌舞战斗戏剧,演示了追求超规范的自由是被规范着的人最深刻的激情。所以,我们看到张旭作为一个书法家的颠狂,看到他人无可企及甚至望而生畏的“逸轨”。这就无怪宋人米芾要骂“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米书九帖》)了。

《古诗四帖》[唐]张旭
但是,如果只看到张旭草书的“逸轨”(颠狂),对张旭所知则不过于皮相。宋人黄庭坚说:“张长史行草帖多出于赝作。人闻张颠未尝见其笔墨,遂妄作狂蹶之书,托之长史。其实张公姿性颠逸,其书字字入法度中。”(《跋翟公巽所藏石刻》)“字字入法度”,是指张旭草书在其超逸狂放中,乱而有法,狂而有度。张旭草书的狂逸,不是乱法,而是以精微深邃的楷法造诣为基础的自由超越——在其看似无法度可循的任性狂放中包含着极精妙的神理。这就是窦衆所谓“神澄”。
张旭传世的草书作品,著名的是《草书心经》《肚痛帖》《千字文》和《古诗四帖》。《古诗四帖》可视为张旭草书的冠顶之作。该帖无署名,曾长期被误判为东晋谢灵运书写,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鉴定为张旭所书。董其昌题跋称此帖“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与张旭其他草书帖同一笔法,并且以“旭肥素瘦”判定此帖为张旭而非怀素书写。怀素是张旭的私淑弟子,同样以狂草出名。“旭肥素瘦”是辨识张、怀师徒笔法的通行准则。黄庭坚说:“僧怀素草工瘦而长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劲难工。”(《跋张长史千字文》)但是,《古诗四帖》不仅表现了张旭用笔宽厚遒劲以及迅猛回旋的特征,而且把率性放纵的书写纳入了刚柔相济、缓急冲和的张力运动中,是极度冲突的劲险与深刻谐调的悠逸的平衡。米芾说:“张旭书,如神虬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米元章续书评》)用米氏此语评《古诗四帖》,是非常贴切的。就此而言,骂张旭乱法的米芾却又洞见到张旭草书的妙谛。
20世纪后期以来,有不少学者质疑《古诗四帖》作者是否为张旭。法籍华人学者熊秉明更指出该帖中的误失、败笔达五十例之多,因而怀疑该帖出自他人临写。(《疑张旭草书四帖是一临本》)以熊说勘察《古诗四帖》,我们可以发现,质疑者是用“理想的狂草”看待张旭草书。然而张旭是没有“理想的狂草”的。《古诗四帖》被指责为失误或败笔的地方(如熊秉明批评该帖“晋”字“一字断为三段”),实在就是董其昌所评议的“悬崖坠石”笔势,是张旭乘兴独到处——非到此,不见张旭惊天笔力。要找“理想的狂草”,只可寻于怀素的草书。“考其平日得酒发兴,要欲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是可尚者。”这是宋代《宣和书谱》对怀素的传述。观怀素《自叙帖》,它复现的是张芝草书的圆转精熟。宋人董逌说:“素虽驰骋绳墨外,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旭则更无蹊辙可拟,超忽变灭,未尝觉山谷之险、原隰之夷。以此异尔。”(《广川书跋》)“回旋进退莫不中节”与“超忽变灭无蹊辙可拟”,是怀素与张旭之间草书笔意的深刻差异,这种差异的实质是妙于巧艺,还是达于自然。
张旭开拓狂草艺术,既蒙滋养于书法艺术的传统精髓,更是深得自然造化的感动启悟。颜真卿记述,张旭即兴用利刃在沙地上画写,见“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而自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另据《新唐书》《全唐文》记载,张旭曾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狂草之所以由张旭肇始(董其昌语),实在因为张旭自我融身于自然,又以自然万物“一寓于书”。虞世南论书法说:“质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笔髓论》)这不正是我们在张旭草书,尤其是《古诗四帖》中观到的笔法神韵吗?
公元9世纪上叶,唐文宗李昂将李白诗歌、斐旻剑舞和张旭草书钦定为“三绝”,并诏命翰林学士撰赞。然而,令人唏嘘的是,这位获得皇帝封号的旷世书家,竟然生卒年及年寿均不详,我们仅能从与他交好的名流诗文中知道他曾活动在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年间(712—756年)。他早年做过常熟县尉,而终止于从六品的金吾长史,他唯一载于史册的“业绩”,就是做县尉时遇到一位反复诉讼求判的老翁,而这老翁此举不过是贪求他手书的判书。张旭的一生,其实就是浓缩到《新唐书》中的157字的一生,这是纯粹到极致、超越到极致的草圣人生。韩愈说“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这是与史传吻合的。
“楚人每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这是李白诗歌《猛虎行》中的诗句,写于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时在安史之乱中,流离四地的李白与张旭相聚于江苏溧阳酒楼,在“杨花茫茫愁煞人”的三月春景中,两人把盏对酌。李白直面的张旭,是一个“心藏风云”的巍巍大者,唯其如此,他的草书才能造就杜甫所说的“豪荡感激”的大气象。韩愈说张旭喜怒忧悲有动于心、必发之于草书(《送高闲上人序》),这只是生活于张旭身后的韩愈的文学想象。心藏风云而豪荡感激,张旭草书,绝不是个人宣乐泄悲之技。
在唐诗中,有李颀的《赠张旭》和高适的《醉后赠张旭》两首。“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李颀)“兴来书自圣,醉后语犹颠。”(高适)“兴”,在张旭,不是寻常所谓“兴致”或“兴趣”,它是豪荡超逸的生命意气。这“兴”,是张旭草书的天机,它借酒而生,以书而张。“兴”,是李白诗言的“心藏风云”的焕发,是张旭草圣的真态。
在杜甫的《饮中八仙》中,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是比肩而立的。“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同一醉酒,同一放达,但细思起来,李白的放达是冲着人来的骄世,张旭的放达是面向天地的自然。李白在唐玄宗的宫中醉酒,当玄宗面呼太监高力士为之脱靴,这是何等骄纵?读史我们知道,清醒时的李白,其实是很懂得尊卑秩序的,是酒给了他过分的胆量。然而,这借酒撒骄的代价,是诗仙李白匆匆结束了他费四十余载心血挣得的翰林生涯、离开他服务不到两年的长安宫廷,从此浪迹江湖,“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旧唐书》)。张旭放达于天然,以纸为天地、以笔墨做风云,他焕然创化的世界中,激烈冲决的险峻之状透现出来的却又是超尘绝俗的“明利媚好”。世知张旭嗜酒,岂知酒独厚爱张旭?
德国哲学家尼采在他著名的《悲剧的诞生》中说过:“热情洋溢的人,何须乎酒。”这位酒神精神的赞美者,未必懂得酒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于中国诗歌与艺术的意义。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