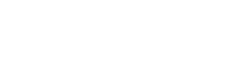摘要:
《齐物论》的思想展开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自我形态:融入世界的言说者和外在事物秩序的建构者,与疏离外在的沉默者和既有秩序的解构者。在持续的言说和开放的反思中不断展开的不同视角和主题中潜含着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自我。首先,从万物互殊的本然到异名对举的不齐,最大的变化就是主体的介入。我的显现必须以我为出发点截断万物并由我的认识和命名将万物转殊为异才能完成,“我”的成立是以有限性为前提的。其次,持续面向置身于其中的世界,以及其呈现的事物之道,诘问物我与人我的殊异与冥同的那个思考和言谈,自然地指向了主体视角的建构的持续性和开放性。进而言之,有限性和界限感成为自我不断遭遇外物的经验触发机制,而这些经验又进一步地激生了自反性的省察。有限性为基础的我的显现与建构是必然更是必要的,只有在主体内部两个面相的不齐中才能揭示整全的浑然。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完全超越了所谓身心与物我的对象化机制。在整全与浑然的底色中,有限的自我才有持续敞开和不断自反的可能性,也只有在有限的前提下,整全与浑然才为自我提供了一种不断回向并尝试超越的活力。
关键词:《齐物论》;自我形态;有限性;整全;浑然
“齐同万物”抑或“齐同物论”,是庄子的注疏与诠释者就《齐物论》的思想主题争讼不绝的问题。然而,无论是互殊之物的齐同还是是非彼是的两行,都是以人为载体和归依的。万物互殊的本然、浑然物化的整体,从言辩胜负到玄冥葆光,都不能脱离主体智识和反思活动。这些反思活动的施行和承受者都是生活在日常经验世界中并展开这些思想时间的那个人。周拱辰直接将《齐物论》的主旨指为“齐我”,“齐物一篇,非齐物也,齐我也。夫见己于世,谓之我,天下皆己也。挫天下之己以见一己,天下之己亏而我之己亦不成,两败之术也。丧我者,弃己而存天下之己也……付我于天下,而天下皆我。嗒然丧我,嗒然见我矣。”1在齐物与齐论的对举中,“我”的智识活动的不断超迈才是推进思想的根本保障。质言之,《齐物论》的思想图景中一直若隐若现地存在着一个“第一人称”的视角,既是融入世界的言说者和外在事物秩序的建构者,也是疏离外在的沉默者和既有秩序的解构者。在持续的言说和开放的反思中不断展开的不同视角和主题中,始终草蛇灰线地潜含着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自我形象。持续面向置身于其中的世界,以及其呈现的事物之道,诘问物我与人我的殊异与冥同的那个思考和言谈,却自然地指向了主体视角的建构的持续性和开放性。
我们尝试说明,主体视角展开的自我反思是《齐物论》思想世界的重要面相。历代注家和解庄者都会在随文显意的注疏之中关切到“我”这一主体视角。不断层迭的视野和延展的视野刷新主体智识,而持续的反思活动和自我修养则达致主体对世界和万物的全新理解,进而指向与万物玄同、与道通为一的精神境界。
一、吾丧我:《齐物论》的自我问题
《齐物论》开篇南郭子綦就以“吾丧我”拈出了存在于主体之内的张力和反思空间,而这种反思空间的显现则是在万物与诸论的言谈之中逐步完成的。“吾丧我”用两个意义相当接近又蕴含主体性和自我指称性意味的日常语汇,以及“丧其耦”的论断,引发了“形躯与心灵”“真妄之我”“主体的限制与自由”“无己”“逍遥与丧我”等哲学玄思和内涵诠释。
检视学界关于《齐物论》的研究和讨论,围绕着主体视角展开的诠释并不鲜见。冯友兰先生通过解读《齐物论》强调绝对的自由与平等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特色。2方东美先生以《齐物论》为一个无限和整全的实质相对性系统(systemofessentialrelativity),“人的个体生命在未进入这种无限性之前,必先备尝种种限制、束缚与桎梏,始能参与此无限。”3劳思光先生在论及道家思想时用自我的四个层次——形躯我、认知我、德性我、情意我——来说明其对精神境界和审美意蕴的追求,强调“庄子于自我,驻于情意一层,是纯粹的生命境趣。”4陈静认为“吾丧我”是理解《齐物论》思想的关窍,“真我”的显现与超然的自由成为反思活动和精神修养的目标。5陈少明将“吾丧我”作为诠释《齐物论》论旨之一的“齐物我”的切入点,“(齐物我)是庄子哲学的最终结论,也即其所揭示的理想人生的最高境界。《齐物论》开篇的‘吾丧我'与结尾的蝴蝶梦两则寓言,首尾呼应,正是这种理想神奇的艺术展示。”6王博将“齐物”与“自由”结合在一起考虑《齐物论》的“无己”义旨,“庄子主张齐物的真正用心,(就是)只有齐物,才可以让人从物的世界中摆脱出来……我们离不开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不在乎这个世界,在不在乎中,心获得了解放和自由。”7置身于世界的自我通过反思活动主动消除对世界的依赖和期待,形成一种与外物的梳理,从而达致自由和逍遥的鹄的。
简言之,关于从主体出发,一偏之见而产生的彼此是非、好恶胜负的反思和讨论,物我、人我之间反复的视角转换,在《齐物论》的文字和思想世界中曼衍不绝,其中悠谬奔逸的文字和兴味盎然的寓言让读者不自觉地联想到充满诗意的精神境界,以及庄子哲学中始终萦绕的“不物于物”“无待于物”“与道玄同”的逍遥与自由的追寻。然而,其中蕴含的对当下和有限自我的否定性超越的意涵,形成了以“丧”与“忘”为基本意象的单向性。在这一语境中,“心如死灰”的玄冥与默寂、“是非两行”的含混和漠然成为最终的目标,自我在与世界的疏离和对有限的当下性的否定中消解于万物齐化的背景之中。质言之,一种玄妙的诗意和超迈的境界是具有高度否定性的自我重构,它一方面让自我得以确立的界限感消失了,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世界中面对复杂经验的自我成为沉寂且丧失活力的绝对他者。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定《齐物论》思想中体现出来的这种幽深超迈的诗意境界,也不是要消解“无待于物”的逍遥和“是非两忘”的从容作为一种智识和精神理想的独特价值。我们更没有能力再辟蹊径,拈取意蕴隽永的思想主旨来重塑《齐物论》揭示的“真我”。与此相对,我们尝试从《齐物论》的文本解读入手理解自我这一主题如何贯穿其思想世界的展开,并由此说明《齐物论》不断展开且持续开放的思想世界为主体提供了两个对举而立又联结一体的面相,从而让自我在日常经验中持续处在物我、人我的张力之中,进而保持自我在心灵和体悟中不断自反的活力和开放性。易言之,“吾丧我”不仅可以被视为一种作为精神境界的结果,也可以是一种反思的原则和持续的过程。
通过《齐物论》的主题展开和文本铺陈,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分析主体视角的不同面相:其一,从万物互殊的本然到异名对举的不齐,最大的变化就是主体的介入。其介入的方式就是用观察和判别的方式凸显万物的分别,用名指的方式让浑然万物之间的转化变成了各自殊异的具体事物的变异,主体的介入才造成了浑然互殊的万物的截断,造成了事物之间的断裂。是非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能被呈现出来的。从是非殊途、强出己意的胜负之争,直至重新揭示物以化齐的浑然与整体性,万物从本然的互殊到价值的互异,复归物化的浑然,都是在主体的智识活动中完成的。对于主体而言,只有把万物的浑然截断,把万物区隔来开,才可能完成自我界限的设定。进而言之,我的显现必须以我为出发点截断万物并由我的认识和命名将万物转殊为异才能完成。从这个层次上讲,“我”的成立是以有限性为前提的,如果我是无限的,那么我就仍然在浑然和本然的晦暗之中,不能被揭示出来。换言之,只有相刃相靡的物我才能保证我从浑然万物的背景中脱离出来,或者说割然自立起来。从互殊到互异,从互异到是非之见的跨越是自我建构的第一个层次;其二,界限清晰的自我必然是有限的。这一有限性和界限感成为自我不断遭遇外物的经验触发机制,而这些经验又进一步地激生了自反性的省察。在自反性的观察中,有限性的自我被视作与浑然和整全对举的存在状态,需要被超越。在《齐物论》的语境中,就是不断诘问自我的那些界限,追问是非、胜负与变异产生的机制,探究物我的区别与浑然的物化,质疑自我认知与言语的正当性,从而引入是非两行、无言之辩、梦觉之间的葆光以明的自觉和跨越。这一跨越的思想后果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否定有限性的自我或彻底消除物我及人我的边界,而是将自我的界限及其内在机制揭示和凸显出来,形成有限的我与浑然的整全的对举。通过物我、人我,以及我与非我的层迭与并置,主体性就被置于有限与整全之间。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层次之间并不存在某种价值上的高下等级,而是一种纯粹的并置。
有限性为基础的我的显现与建构是必然更是必要的,只有在主体内部两个面相的不齐中才能揭示整全的浑然。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完全超越了所谓身心与物我的对象化机制及其后果,构成了以有限为前提的整全性,以浑然为基底的界限感。史华慈在论及道家思想时,也强调了作为主体的“我”在思想展开中的独特功能,“人心有一种致命的能力,它谮称能赋予自己与外界隔绝、完全个体化的实体属性……通过一种自我封闭手段,它就能建立一种只属于自身的自我,与大道的流行之中分离出来……当然,心灵本身也可以成为某种救赎的工具。”8在整全与浑然的底色中,有限的自我才有持续敞开和不断自反的可能性,也只有在有限的前提下,整全与浑然才为自我提供了一种不断回向并尝试超越的活力。
当然,在主体性话语主导的现代西方哲学的环境中,主体或自我等语词的内涵及概念规范十分复杂,因此需要十分谨慎。我们尝试避免一种分析性的范畴化和建制化的自我或主体概念所指摄的二元论桎梏和自我对象化陷阱,也应该避免某种以主体或自我为“知觉的起点与定向的零度”9展开的自我中心式的世界建构。从利科关于主体哲学的讨论中更可以看到从语义学、语用学、行动哲学和伦理规范性等10不同层面不断拓展的主体建构,而这一主体建构的出发点仍然是对象化的二元范式及其反动。
与此相对,我们应该警惕概念分析的窠臼,跟随《齐物论》的文本展开尝试探究自我的形态在庄子的思想世界中如何展开。自我作为一个哲学术语,其内涵十分丰富且充满内在的张力。从语义学和实际经验出发对自我进行解说,需要充分考虑到从存在形态和主体性意识出发都被确证了的自我,加入经验并形成感知与智识活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经验与智识内容都内蕴着具身性、当下性和持续的开放性。与此同时,具有自反性和建构力的智识活动会形成作为对象和“他者”的自我。如果要避免一种主体哲学的概念性框架的束缚,我们可以从具身性所融摄的物性与智性为基点,在经验的语境中划定自我的两个层次:一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具有区隔性的持续确证和界限建构,这一层次上的自我以疏离和殊异的方式揭示自身;另一方面通过投身性和现身性11的方式持续反身消解界限性的限制,这一层次上的自我以诘问和融入的方式扩展自身。这两个层次并没有逻辑优先性的差异,也不存在时间序列上的先后,而是经验世界中自我展开的一体两面。我们尝试用这个简易的框架切入《齐物论》的文本阅读。
在此基础上,努力将容易被定义为玄冥渊默的精神境界和个体体验当做一种激发持续自反性思考的动力,而非吞没思想景观的晦暗。易言之,对于照之于天的圣人境界而言,明达澄澈的静谧与安详显然是可望且有所悟的诗性意蕴,但这种明达澄澈的内里也须有持续自反的、活泼泼的生命力,因此,玄冥渊默中也应该有其发明和活动处。
二、从互殊到物化:截断浑然以显现自我
《齐物论》以“吾丧我”开篇,而以三籁之喻接续,解说“吾丧我”的因由。“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12,气与窍的相激造成了众声齐作而各有所异,究其原因,众声的产生既不是大块噫气的目的,也不是众窍本有的固然,而是一种相激相应的自然过程。正如郭象所强调的那样,这是物之自然而非使然。13“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被强调的“自己”与“自取”强调的是本然固有而无需任何外在性的推动和强制。对于庄子而言,吹万不同的物都是具体和给定的,形形色色、互殊不齐的状态构成了一个整体。万物达成整体性的前提在于并立与共生,在这个意义上说,万物的齐是一种先在的浑然和整全的自性。浑然是万物原初的状态,在浑然的整全性的基础上,万物的自然并不是空洞的,而是有丰富内涵的。万物的互殊与在整体中依照自性展开的转化,保证了整全的内在活力和可持续性。不妨说,万物的互殊是万物之化的基础,也是万物的存在样态。如果将这一意涵纳入到主体的视角之中,则可以说,这种“自”的状态是先于主体的显现与自觉的14,更是无需主体的介入就已经“完成”了的浑然与本然状态。这种浑然先在性的另一种表述就是“物固有所然”与“物谓之而然”中所见的这两个“然”的对举,固有之然是指在“自”的状况下万物的整全与浑然,自达其性,自成其化的独立性与超然于外在观察与判断的状态,而“谓之而然”则是一种命名与判断的结果,这种命名与判断的直接后果就是是非与好恶的价值赋权。
在这里,具有认知能力和判别意图的主体成为一个关键。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层次理解主体的介入:一方面是主体以感与识为基础展开对万物互殊的本然状态的观察、理解与表达,互殊的万物被作为具体和个别的物抽取出来观察,形成在观察情境下的“界限感”,即此物与彼物,这样一来,万物互殊的状态就被终结了,互殊转为相异。主体的介入和判断就让本然的不同被揭示(抑或建构)出来,进而具体的物和与他物的区别成为其成立的根据。有了区别和界限的相异的具体的物,共同构成了一个需要被秩序化的世界。从这个角度出发,关于具体事物的内在结构及其本质的抽象及物的概念才得以成立;另一方面,这一成立和概念运作的必要性并不是这一具体的物需要以此得到一种实存的状态,而是主体需要在物与物的区隔之中逐步将一个具身化(Embodiment)形躯作为一个具体物与其他存在区分来开,从而划定自我与外物的界限。在前后相贯的否定之中,自我的边界可以从三个并置的视角理解:我非物、我非他人、我非无我。换言之,物与物的区分和界限感是主体通过智识活动把自身凸显出来的根本途径,而这种凸显在具象的层次上的最佳载体就是形躯。只有通过截断万物互殊的浑然状态,将互殊转变为可以表述的互异才能将物与物、物与我的界限建筑起来,把自我揭示出来。
从上述的第一方面入手,万物殊然的状态被呈现出来的方式就是名指的运用,通过名指摄不同的物。人的造制和运用是名与指的前提,而以言的形式表达出来才能将名指与事物连接起来,将万物互殊转变为名指互异。公孙龙子以有无之别来说明指与物的差异,“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15名和指只能在主体的智识运用和言谈之中才能与物对举,章太炎先生取《瑜伽师地论》关于相分的论述,“有相分别,依想取境。如其分齐以成音均詘曲,自表所想”,同时“言与意随而非吹,其用固殊……言本无恒,非有定性”。16从取境到别意,言成为相的载体,而相则是来自我对物的观察,相成为物我之间的桥梁,而言则是这一联结机制的具体表现。章太炎先生进而解释“天地一指”一句中前后二指,“上指,谓所指者,即境;下指,谓能指者,即识”。17进一步强调了名指中蕴含的主体性因素。可以说,主体的介入终结了本然的状态,而这一本然状态的终结对于主体的自我显现则是必须的前提。
在身躯与心灵的二元论框架下,自我的显现是具有某种建构性的。康德将自我描述为具有理性能力的先验自我、具有实存性和经验同一性的具身性自我以及具备道德法则的自我等三个层次。18可以行动的身体与保持智识能力的心灵一开始就终结了自我经验的整全性。然而,对于庄子而言,并不存在这种分析性的框架,也没有所谓经验同一性、理性能力与实存身体的本质差异的挑战,自我的存在在于从“成形”的意义上与物对举。在万物互异的世界中,我在与物的界限被凸显出来。“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物我的区分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相刃相靡的状况,从另一个角度看,成形本身也是自我被确立起来的根本途径,只有在相刃相靡中不断遭遇到外物的袭扰才能保持对自我界限的自觉认识。在这一基础上,庄子指出了心随形化情况,外物的变化牵引着心的感受与体悟,“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这里的“心”就是庄子所谓的“成心”,成心是在物物、物我相异的理解中构建出来的秩序和价值判断,而这一价值判断内在机制就是错置章太炎先生所说的指与物的关系,指与相作为人对物的理解结果并非物本身,从相到名与指的固化形成了“物的秩序”。正如前文所述,秩序的出现就蕴藏了主体的自我创制和价值判别,它并非事物原有的本然,而是将指与名作为物的统摄。我们可以看到从先在于主体的万物互殊的浑然,到主体介入之后的互异,直至主体从互异的事物中创制出界限来以名指和言谈确立事物界限并建构事物之间的秩序,最终将秩序及其内蕴的价值层次当做事物的“然”。
从这个视角看,事物从“固有所然”到“谓之而然”的转变是来自主体的操作和区隔,其直接后果并不是改造了物的固然,而是建立了自我对世界的认识,以及物我的区分,正是这种区分和认识,把自我从万物中抽离出来,形成了双重的边界:既有身体之为物的边界,也有对世界“应然”的秩序性界限。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区分了声和音:“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其所觉悟,唯哀而已,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哉?”19自然的声与人有所感的音,其内在的机制在于激生与和应。从声到音的对举中就可以看到人的融入和凸显:外在的声与内在的情相和而成音,人对自然的融入正是其自身的凸显。
正是这样的界限保证了自我的成立,也导致了自我与世界的冲突。界限的清晰一方面保证了自我的主体性自觉,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自我的有限性。有限性可以展现在两个层次上:其一是直截的经验与感受。与物相刃相靡的疲役无功的日常生活与个体经验,日以心斗、师己成心而造成的身心日弛、徒然待尽的虚耗;其二则是智识活动的展开与结果。是非之辩与你我之争体现的自我视角与认识的偏狭。自我视角与认识的两个根源分别是人所固有的智识能力以及自我置身于世界的日常经验,它的展现就是言语中体现的秩序与价值。由此,齐同的问题就转向了来自不同自我的物论,而非万物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言辩与真伪的问题才被提出来。
依照《齐物论》齐与不齐相即相离的文本展开中,万物的本然互殊是第一个层次的不齐,而在浑然的转化之中不断呈现出来的整体性则是本然互殊的不齐的超越,形成了“不齐而齐”的整全图景以及“浑然物化”自然状态。主体的介入终结了这一状态,名指与万物的连接和自我认知中是非好恶的创制造成的不齐不再是本来的互殊,而是自我认识中的万物之别。从这个角度看,要齐的就不再是物,而是对物的认识与判断,进而言之,要齐的就是自我——自我与其他作为他者的自我的集合。自我的第一个形态就是通过从两种不齐的转换完成的。第二种意义上的不齐有前后秩序、因果推故、高下之别、是非之判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的描述和消解就需要从智识活动的内部着手,而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及的那样,智识活动的展现方式和核心载体就是名指与言辩。因此,突破不齐的我见,就需要从言辩和是非入手,通过主体间的视角转换,以及从自我到万物的视野扩张,建立和保持对自我有限性的自觉。在这种自觉之中,不同通过“孰为正”的诘问和“孰是孰非”的责难解释界限分明的自我认识的有限性,以及与自然状态的隔断和冲突,达致照之于天的两可两行的认同,从而使不齐重新向浑然的齐同回归。名指相异和是非判然的万物与人我之别可以重新回到物化的浑然之中,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自我的第二种形态也就被呈现出来了。
三、两行与葆光:自反性省察中的自我开放性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主体的感与识以名指的方式介入万物的本然一方面截断了浑然物化的整全,转变为互异的名指与是非的彰显,另一方面则通过不同事物的各异揭示并确立了自我的界限,从而以一体两面的方式完成了齐与不齐的对举和转化。自我的显现在确立自我界限的同时决定了自我的有限性,而从齐与不齐的对举来看,相异和界限的确立完成了与浑然与无限的对举。从而使得突破和消解这种对举成为可能。
《齐物论》文本中不断敷衍物我、人我、万物的内在关联和转换来不断展开齐与不齐的意涵20。围绕这三个不同视角展开的文本都不约而同地指向自我认识的限制,通过不同视角的并置与主体间差异的强调,激生自我智识中独特的自反能力。这种自反的能力保障了主体可以通过跨越视野界限的方式突破自身的限制建构自我的第二种形态。这种形态的特点就是不断通过是非和真伪的追问来融摄已经被确立为自我界限之外的对象,从而形成了一种融摄性的自我形态。从自反性的能力上看,这种融摄性是既有的自我的否定和解构,而从结果上看,则是将主体自身融入到更大的浑然整全之中,从而克服自身的有限性。跟随《齐物论》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融摄性的自我形态的展开是以自反的省察和反问的诘难入手的,在不同语境中说明视角的重叠性及自我判断的局限,而这一局限的反复强化和凸显则让自我不断融摄价值意义上“异质”乃至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外在者”,实现自我形态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在三籁的寓言之后,《齐物论》直接描述了自我在物我界限上产生的持续冲突与张力,“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自我陷入了疲役的冲突,这一冲突的根由就是是非与守胜,这一描述显明地揭示了有限的自我形态的真实状况及其困境。以此为起点的文本展开是从不同的角度尝试剖析这一困境并激生主体的反思活动。以下我们从内外与彼是、正偏与好恶、言辩与胜负、梦觉与真伪等四个主题截取一些文本段落,说明这种融摄性自我形态的展开。
自我的界限体现在内外之别与彼是之分上,内外和彼是将自我与物和人区分开来。庄子消解内外的方式就是从诘问内外之别入手的: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
如果我们十分清楚内外之别与人我、物我之亲疏,进而有了自我的界限和己意的出处,那么将视野转换到身体之内呢?六腑九窍组成的身体能够做彼此亲疏和内外的区分吗?显然,身体内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是可以有彼此之分的,而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体对于自我而言却是必然。这样一来,明显的矛盾和张力就呈现给自我,从而激发自我反身内省其坚持的内外与彼是之别是否合理。进而言之,身体的内外及身体内各个部分的彼此作为一个隐喻的框架可以指向世界中的万物与人我之别,在整全的自然视角之下,也不应该存在着彼是和内外的区别。在诘问彼是与内外之别的合理性基础上,再强调彼是相因、是非相生的对举关系,从内外与彼是之别生出的是非也是相对而立且无法各自独立的,因此,从相因相生的角度看,自我理解的彼是之见的是非冲突是相因相生而不是相贼相克的。是非相因共生是视角转换的结果,而视角的转换又将基于有限性的自我认知呈现出来了。
是非之别来自彼是对举和彼是相异的认识,而是非的判断则会产生好恶之别。对于不同的外物的好恶则进一步深化了万物之间以及物我之间的鸿沟。然而,在庄子看来,这种好恶实际上仍是一偏之见,其根源还是自我认识的有限性: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庄子用正处与正色的问题引入了不同的主体视角,正处与正色一方面联结这不同存在物的固然本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本性的差异造成不可能有划一的是非。是非的淆乱和不齐如果是本然,那么“劳神明为一”的行为就是多余的。对于不同的主体视角而言,是非与好恶都是从自身出发的,而且由于自身的限制,对于万物的好恶和是非的评判都是有偏颇和有限制的。从自身出发的观察造成的一偏之见才是纷乱是非的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说,纷乱就变成了多元的浑然,自我在这个层次上就可以认识到一己是非与好恶的有限性,从而在这种自觉中保持自我的敞开性。
突破了以自我为出发点的好恶之别,还可以引入不同自我的并置。不同自我的并置造成了另一个形态的是非淆乱,即不同自我对于自身好恶的坚持导致的言辩与胜负:
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
在你我言辩的胜负的视角中,庄子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提出了问题,即主体或自我之间如何实现相知?如果主体之间的隔绝是无法突破的,那么消解不同主体见解的差异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此外,正如吕惠卿疏解此段时提及的那样,“天下之所谓是非者,不过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于我与若,而我与若俱不能相知,则所谓是非者,卒不明”21,自我与自我之间的对举与并置如何实现一种超然的立场对不同视角的是非好恶进行孰对孰错、孰胜孰负的评判?从这个意义上讲,超然的立场并不是来自意见的统合和差异的消弭,而是来自对这种差异及其内在机制的充分认识和透彻理解,从而保持一种态度意义上的平和与超然,而不是追寻一种“必然正确”的真理。
除了主体间的鸿沟,另一个重要的认知限制来自于真伪之辩,即由于主体对于自我界限的感受和经验,不自觉地认为从自我出发的认识与见解是真实不妄的,这是坚持己见的内在基础,也是自我不断强化并激发物我、人我矛盾而虚耗智识与生命的源头。因此,庄子用了梦觉之间的真伪之辩诘问自我感受的真实性的基础: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庄子利用当下经验的真实性为基础,说明梦觉之别可以作为真伪之辩的一个情境。对于梦中之人而言,梦境就是真实,不知其梦则不谓梦境为虚妄。一旦梦境终了而进入现实的时候,人才能觉察到梦觉的差异,进而将梦境斥为虚妄。不妨说,人总是在如流不绝的当下经验中向未知的未来敞开的,那么这个时候真实与虚妄的对举与错置总是虚悬在当下经验之上的一种可能性,它一旦实现了,那么当下经验就被击碎了。更为重要的是,击碎当下经验根本不是目的,庄子是要通过这种虚悬的可能提示主体持续保持对真伪判断的可靠性的质疑。在蝶梦的寓言中,庄子更进一步,尝试说明梦觉之间的隔断,自我的同一性都在这个意义上受到了质疑。我们无法准确地分清梦觉的界限22,因此,梦觉两个经验世界中的自我似乎无法保持统一性。换言之,我们不清楚谁是做梦的主体,那个在梦中的自我与现实经验中的自我在真实性上的等级差别都被消弭了。
需要明确的是,通过上述文本的解读,我们并不是尝试说明《齐物论》是一个层次分明的论证,更不是试图说明《齐物论》以精彩纷呈的寓言通过否定的方式超越自我的有限性。然而,细读《齐物论》的文本,不难看到,上述通过寓言不断铺陈和转换的视角在凸显自我认识局限的同时,并没有提出一种明确的解决方案说明是非、好恶、真伪与彼是何以齐之?不妨说,庄子对自我认识的局限的揭示是放而不收的。然而,整体而言,又不是往而不返的,在凸显问题之后,庄子往往引入“以明、道枢、天钧、天倪、天府、葆光”等涵义隽永而不甚明晰的语词来指摄某种独特的精神状态或认知高度,其中蕴含着十分明显的超越性,将那些无法用具体的思想技巧解决的问题搁置起来,用一种渊默和开放的态度与之共处,而且保持一种不受其扰、不承其困的自由和超然,这样的精神境界因其充满了诗意和浪漫的气息令历代注家涵咏赞叹不已。然而,内蕴的超越性意涵使得这些语词很容易与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联系起来,换言之,在这些语词上,庄子精妙绝伦的思想就被神秘的晦暗和难以言传的超越状态吞没了,进一步的学理解释也因为遭遇神秘主义的鸿沟而不得不回返到诗意与咏叹的层次上。
然而,在我们看来,庄子通过放而不收的方式不断拓展视角,在视角的并置与不断延伸的言谈中反复揭示自我形态的有限性,与此同时,又用“葆光”与“物化”这样的语汇强调通过这种有限性彰显出来的浑然与无限。不同的语境与视角总是提示自我需要保持对自身有限性的自觉,以及由此保持对自身看法的警惕,尝试不断突破自身的囿限,融摄更广阔的视野。视角的并置和视野的拓展之所以可以超越自我的限制,并非因为它消弭了视角之间的矛盾、泯除了人我与物我之间的冲突,而是将这些张力内置于自我的认识之中,保持自我对自身有限性的高度自觉,进而持续反思固有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渊默高深的超越精神境界之外,自我的第二种形态还可能是一种持续的开放性与未完成性。
通过浑然整全的截断,主体构筑了自我的界限,是非与好恶的价值添附巩固了这一界限,但庄子通过视角的并置与对自我界限的诘问提示主体的边界是缺乏稳定性的。这种状况不仅导致了物我关系的对立,更造成了主体自我内部的一种紧张,有限性与浑然性的对举与自我而言就是保持反思和言谈活力的基础,而不是简单的克服和否定。我们应该意识到,将主体的有限性彻底击碎的后果也就是浑然性的消失。从《齐物论》始终贯穿的齐与不齐的主题意义上,这正是所谓不可齐者不能齐的内涵。
从主体的视角看,吾丧我是一种开放且充满活力和弹性的状态,可以保证自我时刻处于与自身有限性的紧张中,实现自我反思的持续性与未完成性,而不仅仅是提出一个难以把捉的境界和精神状态,进而认为这种具有高度诗性的精神状态就是实现万物齐等与物我合一的目标。正如我们前文提及的那样,从自我建构和经验形态上看,自我的界限是不可或缺的,那么真正意义上的物我合一就是自我的终结,而相刃相靡则是保持自我的必要条件。在确立与终结之间的动态自我形成了《齐物论》中所见的第二种自我形态,保证了在浑然与有限之间的思想空间的弹性和自我活力的可持续性。从这个角度上看,自我的两种形态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始终在对举和并置之中的,界限分明与融摄浑然之间,成就了自我的活力与未完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我的两种形态之间的齐与不齐可以成为《齐物论》思想解读的另一种视角。
注释:
1屠友祥:《言境释四章》(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36页。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收入《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8-466页。
3方东美:《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收入《方东美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57页。
4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卷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
5陈静:《吾丧我——〈庄子·齐物论〉解读》,《哲学研究》2001年第5期。
6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3页。
7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
8史华慈著,程刚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2-319页。
9霍伦斯泰因(ElmarHolenstein)著,徐献军译:《人的自我理解:自我意识、主体间责任,跨文化理解》,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11页。其中谈到了胡塞尔认为知觉者以自己的身体为基准点,视为定向的零度,以及这一“知觉情境”在现象学运动中的方法论意义。
10保罗·利科(PaulRicoeur):OneselfasAnother,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2。利科提供了十分全面的主体性哲学综合性建构,他从语义学的“主体”指称入手,强调在语义和语用意义上形成的经验同一性,在此基础上凸显了行动意义上的主体性延展,道德规范性与道德意识成为主体性哲学的一个重要归约。他的建构仍然是在西方哲学的脉络中,依赖主体身心、反身性与人际性三个层次的二元化对象性预设展开的。
11在这里,我们可能使用了内涵模糊的术语,投身与现身是尝试描述自我在反思活动中不断转换视角将自身对象化并加入各种“不属于自身”的情境展开对自身的诘问,同时进入不同的主体存在或事物的视角中“同情地理解”并感受他者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术语的始终很接近海德格尔所强调的作为此在存在的方式的“理解”。
12本文《齐物论》文本都引自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下文《齐物论》引文脚注从略。
13郭象在《知北游》篇的疏解中提及,“有无,无己,明物之自然,而非使然。”(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中华书局,2018年,第927页)
14王博:《“然”与“自然”:道家“自然”观念的再研究》,《哲学研究》2018年第10期;另见叶树勋:《早期道家“自然”观念的两种形态》,《哲学研究》2017年第8期。
15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中华书局,1963年,第18-19页。
16章太炎:《齐物论释》,收入《章太炎全集》(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页。
17章太炎:《齐物论释》,收入《章太炎全集》(第六卷),第21页。
18JerroldSeigel,TheIdeaofSelf,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pp.310-317.
19嵇康:《声无哀乐论》,《嵇康集校注》卷五,中华书局,2014年,第179页。
20陈少明认为《齐物论》的三个主题分别是齐同万物、齐同物我以及齐同人我,他也强调这是《齐物论》中具有哲学意涵的。参见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3页。
21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第100页。
22当然,在现代主体哲学的讨论中,经验世界中的主体同一性及经验连续性成为梦觉界限的一种可能解决方案,但对于庄子而言,梦觉的隔断并不是为了否定主体存在的真实性,而是拓展出一个反思的空间,让主体保持对真伪判断和当下经验的持续反思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