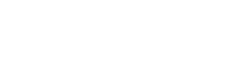哲学的追问,是人对自己本质的追问。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本质,便如何进入一种哲学性质的不倦的追寻之中。千百年来,哲学的一个伟大的梦想,就是寻求一种绝对“真”的语言,把握最终极的实在,进入超历史永恒和超感性绝对的“真正的世界”,建构一个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
“爱智慧”作为对智慧和真理的永无止境的追求,作为一种对世界人生追根究底的探问,它本身就包括了这种“爱”的“理想性”乃至“梦想性”的一维,同时也包含了“爱”的“过程性”或“历史性”的一维。这两个方面在人的人性本质中都有根源,在某种程度上是人追求真理、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理性映现。因此,“爱智慧”奠定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基本框架,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黑格尔(海德格尔也说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的西方哲学都是在一种“爱智范式”下发展和演进的。
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伟大”是勿庸置疑的。不说它构成了哺育和滋养各门科学的母体,曾经有“科学的总汇”和“科学之科学”的荣耀。也不说它在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中一直居于最高主宰地位,甚至由于它的构造作用,西方传统文化被称为“哲学文化”。单从它对一种理性主义思想文化传统的不断塑造,对人的主体性精神的弘扬,对人性的提升和人的自我认识的强调,我们就可以说,今天人们面对的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世界之中的所谓“西方现代性”,实际上导源于这一哲学传统。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行伟大之思者,必入伟大之迷途””西方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在成就其“伟大”、“崇高”之时,是以对最高的价值主宰、最终的真理权威、最真的世界根据的不倦探寻进行的。这种追寻不可能在感性的、相对的、有限的、生成流变的领域获得结果,于是便走到了超感性绝对和超历史永恒的“彼岸幻影”之中,而形式化、逻辑化和概念实体化则是其基本的建构策略。这里产生出来的很多问题是传统形而上学家未曾意识到的,这些问题表现为今天西方哲学和文化经历的重大危机。
追究起来看,危机的根源其实就是那一直隐蔽在西方人“爱智慧”之中的“人与智慧的分裂”。它是现代人经历的种种“两极对立”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紧张的根源。当代德国学者勒内·豪克不无忧郁地说:今天,“无论在西半球还是在东半球,`主观’的人愈来愈无家可归。焦虑变成绝望,导致对麻醉品的享用。程度不同的精神病是我们时代基本的世界性病症。逻各斯信誉扫地。”[1]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性建构与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爱智范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就会看到那给人许诺希望的现代性梦想实际上来自哲学领域的爱智梦想。
今天人的苦闷、焦虑甚至绝望,在于人在科学技术、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社会正义、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等“现代梦想”中看到人类更深重的灾难。阿多尔诺曾经说过,“奥斯威辛之后不再有哲学”。这表明,一千多年来人类的“爱智”之标,原来是人的一种错觉式的价值设定。当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以一种急速运转的形式将几个世纪人类的“梦想”实现出来的时候,那曾经隐蔽在柏拉图哲学王国背后的“专制陷阱”也就由“思想”变成了“现实”。现代人确实如卢梭所描绘的那样,他知道自己是“生而自由的”,但同样也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无处不在枷锁之中”。“爱智慧”本来是人的自由生命的无尽追求,然而这种追求由于忽略了人的生命前提,总是从分裂人和人的世界出发,从人与存在的对立出发,把人置入“两个世界”相互敌对的境地。这种导致人自身的灵肉分裂、人的世界的多重分裂(人与自然的分裂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分裂)的因子,是现代人经历的精神分裂的始作蛹者。
自19世纪以来,当科学、进步和理性在资本主义世界广泛地建功立业的时候,欧洲的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敏锐地发觉“理性的光芒”和“进步的神话”并不能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开始出现,它要追问那种实现在现代科学中的“爱智慧”究竟将人类引向何方。这一时期,哲学要求摆脱对自然科学方法典范的效法,要求抛开那些被认为是真理和智慧的东西,更多地关心人和人类的处境。因此,诗人的吟唱、文学的叙事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写作,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变得愈来愈重要,并且逐渐取代了以往牧师的位置。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境况下,要求哲学成为严格科学的传统主张变得非常可笑。
一旦爱智慧被诸科学分解为对各种认识对象(物)的知识探求,传统哲学寻求一种终极知识的爱智梦想便破灭了。这意味着爱智哲学的终结。整个20世纪都沉浸在终结哲学、告别哲学的深深的忧虑之中。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对以理性、正义和真理之名实施的杀戮有了切肤之痛的亲身经历,使人们对启蒙运动以来有关进步和解放的神话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毫无疑问,人类追求真理、热爱智慧,是为了摆脱谬误和愚昧,为了使人类获得自由和解放。然而,“爱智慧”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福音”,却使得现代人前所未有地陷入深深的两难境地。可以说,20世纪是哲学爱智慧的梦想无可挽回地遭遇到破灭的世纪。这个世纪特有的忧虑在于,对形而上学的反叛和消解其实是向一个伟大传统的告别。在这种告别哲学的一系列思想运作中,首先是一种自18世纪以来就不断地得到强化的现代梦想的幻灭,它同时也表明一种更深远的根基的丧失。我们需要认真地思考20世纪哲学经历的这种幻灭。
毫无疑问,“爱智慧”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演进的历程中,展开了一条“哲学之路”。这是一条伟大的哲学探索之路。但是,这条满怀“希望”、洒满“光明”的爱智道路,却又是一条布满陷阱、充满迷途的运思之道:它遗忘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并通过对“存在者”的追寻,遗忘了“存在”自身的问题。因此,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发展到顶点(同时也是终点),必然回转到它的超始处或开端处。人们从对智慧的欲求、占有和追寻(以人与智慧的对立为前提)回转到重新思考人的生命与智慧的和谐一致就是一个必然的进程。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之转折,反映了西方思想以此种方式向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回转,其标志性事件乃是思想家们碰到了在西方爱智慧的哲学传统中从来没有碰到的“无”的问题。
“爱智慧”的人充满希望。而且,这是一种对追寻的结局不抱任何怀疑的期望。期望的问题在形式上就是“有”的问题,是“是”的问题,或者“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总得“有”个“什么”,人们才期望,如果什么都“没有”,也就根本谈不到“期望”。因此,爱智慧的视野是一种关联着“有”的视野,它甚至把一切渺不可及的“终极之有”涵盖在内。这里面有一种不言自明的“信心”。虽然,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也谈论“无”(例如黑格尔的“无”),但那只是作为“有”的否定性环节来谈“无”,实际谈论的仍然是“有”而不可能真正碰到“无”的问题。与“爱智慧”孜孜于“有”(期望)相反,“弃绝智慧”则走到了希望的反面而碰到“无”的问题。与“虚无”的遭遇必然表现出一种“绝望”的精神状态,它表现为爱智范式的哲学梦想的幻灭。
爱智哲学的基本思路是从“有”追问到“有”,从“存在者”追问到“存在者”。有人称这种追问是一种“有底论”的追问,大致是不错的。这种哲学追问由于总是从存在者深入到“底”,这样就在“有”之间或者“存在者”之间区分了层次、确立起“深度”。它设定了一种最终的存在者,而哲学的追问就是要达到这个“底”。因此,“爱智范式”的哲学家好像在做一场“挖掘”游戏,他们的目的是要比赛看谁挖得更“深”。这种深入到“底”的哲学追问没有触及“无”的问题,更未触及从“无”到“有”的问题。因此,它关注的核心不是“生”(创造或创生),而是“知”。人的生命或生活的主题往往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表现在爱智范式的知识论的追求中。这种哲学追问,从一种理性自识的意义上理解人的本性,最终把人理解成为“认识者”、“求知者”、“理性的动物”和与“客体”相对而立的“主体”等等,它不大可能理解人的自为本性中那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特质。所以,后来西方哲学凡是涉及到人的“从无到有”的创造性本质的地方,都由“神”或者“神性实在”来加以解释。这是爱智哲学始终走不出超感性绝对和超历史永恒的广袤疆域的缘由。
这种“从有到有”的哲学追问没有碰到“无”的问题,但却隐蔽着“无”。只不过哲学家们极少以一种把“底”问“破”的超绝勇气,面对那隐蔽着的“无底”深渊。因为,西方历史在尚未前进到“弃神”阶段的时候,虽然也有形形色色的怀疑论,但这种把“底”问破而使人完全丧失信心的绝望情绪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世界情绪。传统形而上学在一种爱智梦想中,老是要问诸存在的存在,问万有之有,其结果只能是从诸存在中概括出一个普遍的存在。“爱智慧”面对的是抽象概括出来的“有”(存在者)与具体感性的“有”(存在者)之间的层次区分。柏拉图将抽象物、概念物实在化并将它看做是最高等级的实在的理念论,以种种变化了的形式构成了西方思想史上哲学爱智追问的“底”。然而这种抽象的“存在物”和“有本身”,只是存在事物的“本质”,是一种“思想”,一种“概念抽象”。任何由“思想”、“概念抽象”构成的“最高实在”在经验的世界里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对应物,因此在其背后都隐蔽着“真正的世界”之最终幻灭的命运,必然会碰到被人们当作最真实的东西予以追求的“有”实际上是一个“幻影”并隐蔽着“虚无”的问题。
“爱智慧”确立了一种追寻初始本原、充足理由、最终同一性、最高价值原理和永恒抽象本质的哲学探索的道路(人们通常称之为传统本体论)。如前所说,这种哲学爱智达到顶点,必然不满足于只是不停地更换“最终基础”或“最后根据”(“底”),一旦哲学的追问在爱智范式中出现了把“底”问“破”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哲学爱智梦想的幻灭。
西方哲学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经历了一次转折,此后17世纪形而上学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都基本上是在这次转折的基础上用“人”、“主体”或“理性”作为“最后根据”来取代“神”的位置。然而“神”并没有被废黜,它只不过改换了一幅面孔,以“人”的形象出现在哲学的追问之中了。因此,近代出现的哲学转折并没有改变传统哲学的方向,它是传统哲学原则的进一步展开,是其终极可能性的展现。当这种可能性达到极致的时候,“爱智慧”到“弃绝智慧”的转折就呈现出来了。因为哲学爱智梦想的幻灭必然表现为哲学之“问”出现了把“底”问“破”的情况,这意味着不再有一个终极存在(超感性领域)给人的生命意义提供最终保证。这样一来,作为“底”(超感性绝对和超历史永恒)的“上帝”就被取消了,“上帝死了”。紧接着的问题必然是:人如何穿过无际的“虚空”?或者,面对“无底深渊”的人如何才能活下去?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类似问题是:“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如何活下去?”这些问题使“生命意义”的追问成为哲学的主题。而“生命意义”的主题化在理论前提上必然通过“一切价值的重估”表现为“弃绝智慧”。
与“无”的遭遇,集中表现为西方现当代思想经历的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的转折。19世纪末和整个20世纪处于这个转折时代之中,转折时代的特点,可以用这个时代三个代表性的思想家的判定词来表达,这就是“上帝死了”(尼采语)、“哲学的终结”(海德格尔语)和“人之死”(福柯语)。
尼采代表了从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维度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的转折。他选取的弃绝智慧的视角是“上帝死了”。尼采抨击基督教道德、理性主义和精密计算的一个主要的方面是由于其对人的健全生命本身的戕害。在这一意义上,尼采指责西方柏拉图主义思想史是“一段错误史”,乃基于对全部欧洲文化和哲学的历史的反省、检讨和清理,亦即基于“弃绝智慧”。“人们前此热心重视的东西,甚至都不是实际的东西;它们只是幻想,或者,更严格一点说,它们都是来自不健全本能的谎言,或者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它们都是来自于有害本能的谎言——所有关于`上帝’、`灵魂’、`美德’、`罪恶’、`来世’、`真理’、`永恒生命’……这些概念。但是,人们却在这些概念中寻求人性的伟大,寻求人性的`神性’(divinity)”。[2]历来的哲学家都自称是“爱智者”,然而哲学家的“爱智”只不过是用“永恒”将“历史”制成了一具“木乃伊”,用“真理”将“生命”变成了“偶像的侍从”。尼采指出,“几千年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脱他们的手掌。”[3]这即是说,哲学家们热爱智慧、追求智慧,实际上是通过逻辑化、形式化的方式制造一些最空洞的概念(概念木乃伊)或最高范畴(概念偶像)并由此构造所谓终极真理的体系。哲学家其实只不过是“概念木乃伊”的制作者,是“概念偶像”的“侍从先生”,哲学家由此制作了供自己崇拜的对象;在他们崇拜之时,他们剥夺了一切生命、生成和历史。这种否定生命、厌恨生成、超越历史的爱智道路必须被彻底废除,真正的思想家必定是在“上帝死了”的绝对虚无中弃绝“最高智慧”或“终极真实”的一切图谋的“艺术家”;他们对生命中一切健全的、强有力的、自由的东西有着敏锐的感触,在酒神式的沉醉狂欢的境界中寻求生命的神圣肯定。
如果说尼采“上帝死了”揭开了由生命意义的视界并且主要是在道德和价值问题上对传统爱智哲学的“弃绝”,那么海德格尔则是通过宣告“哲学的终结”而从存在“意义”和“真理”的界面上遭遇“弃绝智慧”的转折的。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主要是通过区分存在与存在者,以指证传统形而上学对存在问题的遗忘。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试图通过思考“此在”如何使“在”“明”起来,来思考那被传统形而上学遗忘了的“存在意义”。海德格尔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前半个问题,重要的内容是对此在“历史性”、“有限性”的分析。海德格尔对“此在”如何使“在”澄明的分析,破除了传统形而上学老是要到一个超历史永恒或超感性绝对的领域中寻找“起源”的“梦想”,确立了海德格尔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基调。但是,这一时期,海德格尔仍然还有建立一种基础存在论的梦想。后期海德格尔从“物的纯真”和“人的诗意栖居”两个方面“思”存在的真理。思考的主题仍然是人(此在)的出现如何使存在澄明起来,但侧重点不再是通过此在解释学对此在存在的追问进行,而是要求人们“听命于存在的邀请”、“居于存在的近邻”。因此,后期海德格尔极力摆脱了前期思想中仍然残存的人类中心论倾向,认为“人不是存在的主宰者”,“人是存在的守护者”。后期海德格尔思考的目标也不再是建立一种基础存在论,而是要在现实的层面上“克服现代技术”,在理论的层面上“克服形而上学”。因此,海德格尔是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这一维度遭遇“无”的问题。这在他后期思想对技术本质的追问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海德格尔一生都在思考形而上学,他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实际上是对形而上学在技术座架中的实现的追问,哲学(形而上学)在科学的独立和技术演变为座架的过程中达到了其最极端的展现,标志着它的终结。海德格尔实际上是在“哲学的终结”这一点上面对“虚无”问题的,他所说的“哲学的终结”是指那种“从有到有”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因此在西方当代思想家中海德格尔对“无”有着很独到的理解。
而在福柯看来,海德格尔虽然把人理解为“历史性”的存在,但仍然保留了“存在的意义”,所以“人”在海德格尔那里并没有完全消失。福柯对尼采的解释完全不同于海德格尔对尼采所作的解释,他认为尼采的“上帝死了”说的是那杀死上帝的“人”的死亡。福柯分别沿着知识的轴线、权力的轴线和伦理的轴线,考察了“我们怎样被建构为我们自己的知识的主体”、“我们怎样被建构为操作或服从权力关系的主体”和“我们怎样被建构为我们自己的行为的道德主体”。福柯的著作揭示了权力的无所不在,并且一种异常醒目的方式凸出了理性、知识、主体性以及社会规范的产生等所具有的成问题的或可疑的方式。他以翔实的分析说明了权力是如何渗透到学校、医院、监狱及社会科学之中,同社会及个人生活的所有层面交织到了一起。福柯沿着尼采开辟的道路,对各种形式的看起来有智慧、有价值的思想(如人道主义、自我认同、主体性等)提出了质疑。当然,福柯的思想从基调上充满了悲观色彩。按照他的观点,现代性并未带来医学、民主和自由方面的任何进步,而社会的权力-控制机构使得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监狱。事实上,福柯经常为一些相互冲突的理论信念所困扰,人们注意到他的著作在总体化与非总体化的冲动、推论性政治与生物性政治、摧毁主体与重建主体之间摇摆不定。这些特点反映了他在解构西方传统或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的游移和彷徨。
一则古老的希伯来寓言讲叙了“通天塔”是如何变为“巴别塔”(争吵之塔),这个寓言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哲学经历的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的转向。建造通天塔需要的智慧是一种伟大的知,我们相信这种智慧或知的伟大,在那里人们彼此理解,但由于语言混乱,到最后拆掉塔顶的时候,他们才真正彼此理解了:这是一座“巴别塔”(争吵之塔)。巴别塔没有建成,它最终倒掉了。“我们建立一个体系,甚至设想一种关于各个系统的一般理论,作为能达到终极触到天的一般的普遍理论。”我们试图用这理论来重新理解巴别塔,可是,“这种体系如今已经衰败了。”[4]人类建造哲学形而上学理论体系的活动,与这里所说的建造巴别塔的活动,具有类似的历史命运。或者说,它本身代表了对人类试图重建“通天塔”的各种思想文化运动所隐蔽的前提的揭露。
从这个寓言故事中,我们看到三个因素在发挥作用:一种最高形态的知识理想;它所具有的诱惑;以及它所隐蔽的无知或虚无。人们用概念、用思想、用想象等来建造,开启出伟大之知的“通天塔”的建构工程。这种到达伟大的知的努力,使人在知的决断中进入爱智慧的建造活动之中。然而,这种诱惑最终却使原始的和谐倾塌,于是我们面对曾经被灿烂的外表蒙蔽住的伟大而令人震惊的“无知”。“我们就是带有嘈杂声的各种语言的百衲衣。一座塔加上噪声,一种体系加上喧嚣与躁动,一些建筑精美的墙垣,加上一些哭墙,那里的呻吟、呜咽和悲泣声可以使已经断开的石头碎裂。这时我们明白了。历史开始了。”[5]
通天塔是同一性智慧的象征;而它一旦变成了“巴别塔”,则是同一性的智慧最终解体的象征。哲学家并不建塔,吸引哲学家的是那种建塔的智慧,和那种拆除巴别塔的智慧,是那种伟大的建构和伟大的解构。我们由此进入历史吧!我们可以在哲学家爱智慧的历史旅程中看看通天塔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变成了“巴别塔”(争吵之塔),于是,“爱智慧”也就变成了对最高智慧的弃绝!人是不可被置换的,人的爱智慧使他接近于“神”,但人的历史性存在的前提决定了他不是神。人又重新回到了充满劳绩的大地,大地无怨无悔地接纳了他。巴别塔没有建成,人们从神圣的建造中回到坚实的大地,每一个个人在散落于尘土的无穷争执或争斗中发现自己突然领会到了“巴别塔”的意义,于是人进入时间和历史。我们所要依赖的不是一个将我们引向白云深处的智力的安宁,而是在广泛地散落到大地上后那种历史性的孤独。唯有在此孤独中,我们才意识到无智慧的状况是如何深切地构成了我们的时空限定,才理解到“爱”和“智慧”是如何唤起我们对人类起源的回忆,并且支配着我们的整个历史。
巴别塔彻底倒掉了,通天的路消失在荆棘丛生的废墟中,人和人类又一次面临决断:一切伟大的知的背后,必定隐匿着伟大的无知;“通天塔”,换一个角度看,就是“巴别塔”;然而,谁将承担起这样的使命,将沉浸在慷慨豪迈的不朽伟业中的人唤醒呢?当隐蔽的虚无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喧嚣声漫过了我们的眼睑,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我们从建塔人的伟大希望开始,我们就置身其中,我们的父辈散落在大地上的开始就是我们的开始。问题的关键是:在爱智梦想的幻灭处,我们如何为人类的这种希望辩护?我们今天更紧迫地面临着这问题的困扰。
西方哲学经历的“哲学的梦想”的幻灭之所以值得我们的重视,是因为这里隐蔽着“人的奥秘”和“哲学的奥秘”,表达了“人的命运”和“哲学的命运”。“爱智慧”反映了那种需要抽象永恒本质、需要绝对最高主宰、需要在一种自我异化或对象化中认识人自己的“人的处境”。然而,爱智范式的哲学并非一无是处,它是人类在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推动文明的发展、知识的进步和理性的累进的伟大的探索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确立的一种“主客二分”的知识论框架以及在一种对象意识中对知识确定性的不倦的追寻,还有对“根据”和“理由”的究极式的追问,使得它成了滋养和哺育诸科学的母体。然而,当分工越来越细密,社会结构的分化越来越向纵深展开,科学越来越演变成了一种全面的技术统治,滋养和哺育诸科学的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也就在纷纷独立的诸科学那里完成了自身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家们意识到传统哲学追求的爱智梦想的虚妄本性,因此消解或弃绝传统爱智范式的哲学所设计的“最高智慧”就成了哲学家们共同面临的一个主题。爱智梦想的幻灭就是哲学-形而上学的幻灭。哲学-形而上学的幻灭也就是人对一个超感性绝对和超历史永恒的知识领域和真理领域的信仰的幻灭。这是发生在当代人身上的一件大事。20世纪西方哲学以自己独特的运思揭示了“通天塔”成了“巴别塔”的“形而上学的命运”。哲学的命运其实是和人的命运紧密联在一块的,我们今天处于这一命运之中。这命运要求哲学的追问和人的追问必须在一种内在关联中回到人所生活的现实生活世界,要求哲学的追问同时也是人生命自身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