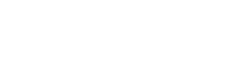离自然的远近,取决于心。今人离自然远,每当春暖花开,面对眼前的青草杂花,看着欢喜,可就是一个也叫不出名字来。这不就是心与自然离得远吗?
读点《诗经》吧,那里有与大自然的亲近,其中的草木鸟兽虫鱼特别多。当年孔老夫子就号召他的学生们学《诗》,说学《诗》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多巧,仿佛孔子早就预知了后人只会对着春花春草激动而难以名之的尴尬。到三国时期就有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再后来这方面的研究颇有继续者,成为“诗经学”的专题。
孔子说“鸟兽草木”,限于篇幅这里只谈“草木”,即《诗经》中的植物。那么,《诗经》中的植物有多少?据陆文郁《诗草木今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有一百三十二种。据日本人冈元凤纂辑《毛诗品物图考》,则有一百四十八种,其他此类著述应还有数量的差别。这不是人们数不准,问题出在认定上。例如《卫风·木瓜》篇中的“木瓜”“木桃”,有学者认为是树木的果,也有学者认为“瓜”不是真瓜,“桃”也不是真桃,都是木头做的仿品,此类认定的差别还有很多。这样一来,《诗经》中有多少种植物,就难用“数一下”的办法来确定了。
这百馀种的“草木”,又分“草”和“木”两大类。属于“草”的,像《小雅·南山有台》的“南山有台,北山有莱”,“台”是草,又叫夫须,可编制蓑衣、斗笠等,《小雅》《周颂》中都有人们戴着“台”编的斗笠的形象。莱,又叫藜,就是《红楼梦》里秦可卿屋里挂的《燃藜图》的那个藜,是野生菜蔬的一种,幼苗可食,长高变老,又可以“杖藜扶我过桥东”,古人也是称之为“草”的。这些能食用的“草”,亦即果实根块能食用或药用的植物,在《诗经》中的占比是最大的。至于“木”,在《诗经》中也同样繁多,包括丛生的灌木、藤蔓类以及高大的乔木等。再从生长的地方说,这些草木,有水生的,有陆生的。生在陆地的,有高山、平陆和下湿之地的不同;水生则有皋、涧、沚、渚、沼等的不同。由此,《诗经》呈现的世界才是生长着的,蓬蓬勃勃,显示着人与大自然全方位的亲近。

读《诗经·关雎》,“参差荇菜”反复出现。“荇菜”是什么?有人说就是杏菜或金莲儿等,开黄色花,据说嫩时可食。不过,笔者认为,读“参差荇菜”句,先要有的概念是:它是水藻类植物。在《诗经》里,不止一次出现此类植物,如《召南》中的“蘩”“蘋”及“藻”,其中的“蘩”,又称由胡、白蒿等,“蘋”,又叫田字草、四叶菜等,“藻”,在这可能泛指上述水藻之类。此外,《小雅·采菽》有“芹”,《鲁颂》有“茆”,其中的“芹”又叫水芹,至今仍在食用,“茆”,据说是西晋大名士张季鹰,秋风一起就思念家乡的美味莼菜。然而,上述《周南》《召南》说“采荇菜”“采蘋”“采蘩”,是要表达“吃”的意思吗?《诗经》植物解释的一些书,言及此,总会说“嫩时可食”,这也不错,可就《诗经》篇章而言,《关雎》《采蘋》《采蘩》所以言“采”上述水藻,该是另有暗示,即女子的家庭主妇身份。 何以这样说?《关雎》中“淑女”为“君子”“好逑”,淑女不是要成家庭主妇的吗?《采蘋》言从“南涧之滨”的水泽采集水藻,然后烹煮,用来在宗庙“牖”(窗户)下办祭祀仪式。这祭祀,历来的说法是女子出嫁前教育结束的一个节目,如此,也与女子不久将来的主妇身份有关。《采蘩》说“于沼于沚”,采了“蘩”做什么呢?用于“公侯之事”“公侯之宫”,这个“宫”就指宗庙。主妇采集水藻用于“公侯之宫”,让人联想起《左传·隐公三年》载“蘋蘩蕰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的说法。两下联系,采集祭祖的“蘋”“蘩”“藻”之类,似乎就应是家庭主妇的职事(周人日常侍奉宗庙及祭祖时准备食粮祭品的也是家庭主妇)。这样的习俗可能由来甚古。周人祭祖何以用蘋藻之物?有人说是因为生活艰辛,食及野菜,这有可能。可是,周人上层早已贵族化了,贵妇还为果腹而采藻,不妥当,因而可以寻求解释。原来,周人祖先死后归于渊(参《山海经》言后稷)。若再往前溯,周人族群与夏关系密切,早就有学者注意到,大禹治水时多有“水族类”生灵帮助的神话。水族类的生物,自然离不开水藻类的植物。如此,周人祭祖时家庭主妇采集水藻“荐鬼神、羞于(进献)王公”,就是遵循古老的安顿祖先灵魂的祭祀传统。也就是说,这些看似不经意地出现在诗篇中的植物,背后却有着十分古老的观念。 由此,在《诗经》中,关于“草木”的采集,就可以分两类看:采水生植物和采陆生植物。水生植物采集已如上述,那么陆生植物的采集呢?《诗经》中陆生植物的种类,要远多于水生的。《关雎》“荇菜”之后,就是《卷耳》的“采采卷耳”、《芣苢》的“采采芣苢”、《草虫》的“言采其蕨”,之后更有“采葑采菲”(《邶风·谷风》)、“言采其蝱(méng)”(《鄘风·载驰》)等。在《王风·采葛》中,短短的诗篇更是连续出现“采葛”“采萧”和“采艾”,甚至在《小雅》中也有“终朝采蓝”“采绿”的句子。很有意思的一点是,“采”字一出现,如是采陆生植物,往往继之而来的是思念情绪的表达。最典型例子如《采葛》,“采葛”“采萧”和“采艾”,引起的就是“一日不见”,如“三秋”“三月”“三岁”的思念。《周南·卷耳》《召南·草虫》也都是先言“采”继而表远人思念的例子。这究竟是《诗经》文学的一个小小“定律”还是偶然的类似,值得研究。无论如何,在这里,诗篇将思念中的女性,有意无意地放置在绿色的天地之间,人与自然物色相映衬,诗意因而格外悠长,则是肯定的。
另外,分别植物的水生与陆生,对理解诗旨是有益的。如《召南·采蘩》出现的“蘩”,在《豳风·七月》“采蘩祁祁”也有出现,它们就有水陆之别。《采蘩》之“蘩”,可“荐、羞”于祖先鬼神,而《七月》的“蘩”,《毛传》说可用来生蚕,现当代学者研究,就是将蘩用水煮,用其汁液浸沃蚕子(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可助其孵化。此外,《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毛传》说“苹”即“萍”,是解释为水藻之类了。郑玄觉得不妥,改释为“藾萧”,属于陆生的蒿类,因为鹿不食水藻类植物。可是,访之东北的养鹿人,蒿类植物也难说是鹿的最爱。如此,《鹿鸣》的“苹”字,理解为诗人的灵活用字,也许更好一些。 《诗经》中草木众多,各有其功用,如上所说大多数可食。更多的例子如上面所引《草虫》中的“蕨”,至今一些餐馆还可以吃到;又如“葑”“菲”,就是根块类的蔓菁、萝卜等,是腌制咸菜的食材。大家都熟悉的韭菜,也在《豳风·七月》“献羔祭韭”中出现,令人感到亲切。这样的“古今通吃”的菜蔬,《诗经》中还有瓠瓜(参《邶风·匏有苦叶》《小雅·南山有台》等)。因当时的人都熟悉此瓜,所以诗人还用“齿如瓠犀”(瓠犀即瓠瓜籽)来形容美女牙齿的好看。像《豳风·七月》中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都是写“吃”的,满是乡村的瓜果味。它们有的属于人工培植,如“稻”、“枣”、“瓜”、“壶”(嫩时可食,成熟可以做瓢)、“菽”;其他则为野生,如“郁”“薁”为野果、“葵”“荼”系野菜等。在古人的生活里,这些往往是粮食的补充甚至替代品。

有些植物可以做衣料。《采葛》中的“葛”,为藤类,其纤维可以纺织为粗细麻布,在《周南·葛覃》篇对葛有更多的表现,诗言“是刈是濩,为絺为绤”说的就是葛麻为衣的过程:先要割取,水煮脱皮、抽取纤维,织成的麻布,细者为絺(chī),粗者为绤(xì)。有趣的是,诗篇明着写葛衣的制作过程,同时也暗表了女孩儿向新娘身份的成功转变。《诗经》中还有其他做衣料的麻,如《陈风·东门之池》中的“麻”“苎”;像《小雅·采绿》中的“蓝”和“绿”,又有做染料的功能。衣食功用之外,有的还具药用价值,如《鄘风·载驰》“言采其蝱”的“蝱”,其本字应为“莔”,今称贝母,文献记载有祛痰、止咳和止吐血的功效。“采采芣苢”的“芣苢”,一般认为就是车前子,过去的乡野随处可见,据《毛传》说可以帮助妇女怀孕,“采采芣苢”的篇章,可能与妇女祈求生育有关。也就是说,一些植物出现在诗篇中,与诗篇主题还是颇有关系的。 衣食药用之外,“蒹葭苍苍”的芦苇,可以编制席子、苇帘等,茅草可以“索绹”、覆盖屋顶(《豳风·七月》)。有些花草,除了上述的功用之外,如《豳风·七月》“四月秀葽”的“葽”,今名远志,其开花时间可帮助古人确定时令,有物候学上的用处。再如《墙有茨》的“茨”即今所谓的“蒺藜”,看似无用的植物却也入诗,用它来比兴坏事。
种类同样繁多的是树木,也同样用处颇广。大家熟悉的“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卫风·伐檀》),檀木被伐之后,为什么要“置之河之干(岸)”呢?有学者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原来檀木坚硬,木料使用之前必须花一定的时间用水浸泡令其变软。有史家说,周人用檀木制造坚固的战车,也是其顺利“克商”的原因之一。关于木,古代有许多今人不熟悉的常识,例如榆树。《诗经·唐风·山有枢》写“隰有榆”,另外《陈风·东门之枌》的“枌”系白榆,也是榆树的一种。与檀木不同,榆树砍伐后得迅速去皮,否则木材会开裂。另外,榆树的翅果(榆钱)可食,鲜嫩可口,其木料可用于制造器具或房屋建筑等。还有,古代关隘多种榆,用以阻挡骑兵,如榆林、榆中的地名便与此有关。还有几种树木,诗篇显示与“礼乐”有关,如《鄘风·定之方中》“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句出现六种树和两种乐器。诗篇是写卫国都城在遭遇北狄入侵后的重建,种上这些树,有的是为果实(如榛栗),有的则是因其木料可制作乐器(椅桐梓漆),显示的是邦国崇文教的情怀。与人文情怀相关的还有松柏,时间较早的《大雅·皇矣》有“松柏斯兑”,是说经过开垦后,岐山的松柏行行列列,还是写实的;到《小雅·天保》这首晚期诗篇,在“如南山之寿”一句之后,即“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之句,很明显,“松柏”已经变为象征生命力量的意象了。 在诸多树木中,不可不谈的是桑。“桑梓”,代表故乡,这个词出现在《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在《诗经》中出现很多,“桑中”(《鄘风·桑中》)、“桑叶”(《卫风·氓》)、“桑者”(《魏风·十亩之间》)、“桑野”(《豳风·东山》)、“桑扈”(《小雅·桑扈》)、“隰桑”(《小雅·隰桑》)等,不一而足。桑之贵在其丝,诗篇就有《氓》的“抱布贸丝”。此外,“桑”还与男女风情有关。《卫风·氓》写的就是桑田蚕女与氓之间的爱恨,而“桑中”则代表着一种正统之外的婚恋。人们直到汉代还喜欢桑,所以在汉画像中每每可见富贵人家高大扶疏的桑树形象,而“秋胡戏妻”故事,讲的是久别夫妻桑园中的相会。由此可见,桑与男女风情的关联,在文学史上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母题呢!总之,大自然的草木,映现在诗句中,多种多样,是不论功用大小的。 这又回到前面“古人离自然近”的话头。现今人们生活在城市里,一切的生活用品皆为工业加工品,那么,心理上离活泼泼、草荣木茂的大自然肯定就近不了。在《诗经》时代,除了麻、黍、稷、麦、菽等五谷要耕种之外,大自然的草木,也是人们的“衣食所安”,或种植,或采集,或以之察时令等,如此,自然就亲近它们,熟悉甚至爱惜它们。心的距离近,在诗篇中对这些植物脱口而出就很自然,这成就了一种亲近大自然的文学。 亲近,所以成就文学。因为亲近,古人就用触手可及、随处可见的植物来写心抒情。《诗经》中,当古人要强调兄弟关系重要时,就用“棠棣之华”来为全诗起兴,因而“棠棣”从此成为“兄弟亲”的象征。唐玄宗时修“花萼楼”,正要表达这样的意思。当古人要表现春天男女相会之地的热烈时,会想到以“隰有游龙”来衬托。“游龙”就是红蓼,俗称“狗尾巴花”。想想吧,“狗尾巴花”,开成游龙一样的一片红色,那光景何等美丽!当诗人要表达孤独的感受时,会写出“有杕(dì)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唐风·杕杜》),用“杜”比兴“踽踽独行”的孤独。“杜”,又称“杕杜”,就是杜梨。若干年前,在北方,农村村口地头乃至破庙中常见。在《召南·甘棠》出现的“蔽芾(叶子茂盛貌)甘棠”,也有人说是“杕杜”的同类。这种树,多独自生长,春天开花,满树鲜白,秋天结果,果实比豌豆大不了多少,一串一串的。最有特点的是它的老干,斑斑驳驳,弯弯曲曲。因树干斑驳和弯曲,秋天结果时,孩子们爬上爬下,却也方便些。其实果实酸涩难吃,然而爬树的乐趣吸引力实在是大。所以《甘棠》篇嘱咐“勿剪勿败”,应该主要是对这些淘气孩子讲的吧。

现在,情人节一到,花店的玫瑰格外紧俏。其实古代也有表达爱的花朵,且有两种,那就是见于《郑风·溱洧》的“兰”与“芍药”。初春光景,“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jiān)兮”。郑国的男女在溱水、洧水畔相聚,男的女的都“秉蕑”,即手持兰草,亦即泽兰。人们喜爱它,是因“兰有国香”,可以消灾祛病,因而可赠予心爱的人。在郑国,还有一段传说:郑文公的妻子梦见祖先赐给自己兰,后来就生了儿子(郑穆公,参《左传》)。看来,这“国香”的草,还与生育有关。在男女相会的日子,香兰之外,他们还持另一种花:芍药。《溱洧》篇最后一章唱:“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芍药花现在也常见,它美丽如牡丹,又称花相。食之可以祛毒,美丽而实用。“芍药”的“芍”与“媒妁”的“妁”,“药”与“约”,都是发音相近的字眼。因此诗篇写男女相会最后分别的一刻,嬉笑之馀又互赠芍药,与“芍药”之名或许有关。又,《韩诗外传》称芍药花为“离草”“将别”,应该是暂时分手时的定情物吧? 《诗经》中的花草树木,将我们带到了山野水畔,带回了大自然。文学是心灵的事业,千姿百态的草木成就了《诗经》心灵文学的独特。试想:“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是何等动人的境界?与自然的亲近,已嬗变为文学的魅力。“草木”营造艺术氛围,《诗经》就这样为古典诗歌文学开了篇。以此,中国古典诗歌抒情,走上了自己的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