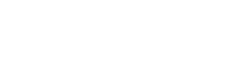《你在高原》:大气俊朗 宽广通透
陈晓明
长篇小说《你在高原》10卷本,450万字,这显然是汉语小说写作史上不同寻常的举动。固然现代长篇小说讲究构思,愈来愈趋向于精巧,并不鼓励拉长篇幅。但中国的长篇小说还是着眼于历史叙事,还是要靠着社会生活和现实逻辑,没有大的容量又难以表现广度和深度。没有理由认为长的作品一定就比短的作品更占优势;也同样没有理由认为短的作品就比长的作品更好。长短一定要回到具体作品来讨论。就张炜的这部长篇小说来说,随便抽出几卷,都可以和当代最出色的作品比高下,而10卷合在一起,它所具有的艺术分量,当不容置疑。一个作家有如此强盛的创造性,有如此坚定的文学信念与创作热情,这无论如何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令人肃然起敬的成就。
我以为要从艺术上说这部作品的显著特点,那就是:这部系列长篇如同有一个“我”在高原上叙述。
其一,大气。“我”的叙述穿越历史。叙述人可以在历史中穿行,在宽广深远的背景上展开叙述,有一种悠长浓郁的抒情性语感贯穿始终。汉语文学在历史叙事方面有自身的传统,并且达到较为成熟的境地。需要进一步去发掘的是,汉语文学在突破历史叙事的现实主义或客观主义的习惯模式方面还有多少新的作为。张炜这部作品在这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张炜的贡献当然承继了先前的优秀作品,如《白鹿原》等,但它自有独到之处,那就是能用“我”的主观化反思性叙述穿越历史。张炜的叙述人“我”携带着他强大的信仰进入历史,并且始终有一个当下的出发点,使这部作品有精神高度,有情感广度,有思想力度,因而气势高远,气韵生动。
其二,俊朗。富有抒情的叙述。张炜以他的思想、信仰和激情穿越历史,沟通了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因此他能建构这么庞大复杂、激情四溢的历史叙事。这部10卷本的长篇小说,尽管每一卷都有独立的主题,都有独立成篇的体制,但叙述人宁伽贯穿始终,其中的人物也在各卷中反复登场,故事也有明晰的连贯性。但张炜在这么漫长的篇幅中,始终能保持情绪饱满的叙述,那种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想象在人文地理学的背景上开辟出一个空旷的叙述语境。浪漫主义从中国现代就被压抑,总是以变形的方式,甚至经常被迫以现实主义的面目出现。张炜以他自然自在的方式释放出充足的浪漫主义叙事资源。或者说以浪漫主义为基础,融合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元素。
第一卷《家族》是全书的铺叙,在家族起源的叙事中,却有非常精细的场景出现。在《家族》中,历史、革命、暴力与大家族的崩溃,以及传统社会的瓦解结合在一起,叙述的激情与历史的悲剧感结合得颇为精当。革命的历史从颇为浪漫的故事开始,而后充斥着暴力、变异、断裂和转折。如此古典、如此浪漫的现代前史终结了,20世纪的中国进入了动荡不安的革命进程。在《我的田园》中,秉持那种反现代都市文明回归田园的陶渊明式的生存态度,这也是典型的自然主义式的浪漫精神。在《忆阿雅》中,那个来自大自然的不可能的动物“阿雅”,一直在注视着人类,那双眼睛,一直是张炜要在自然背景上寻父与审视“50年代生人”的思绪的引导。
其三,宽广。人文背景深远。人文地理学、历史叙事与自我的反思性构成的立体叙事空间,这是张炜非常独特的创造。小说中的主人公宁伽的职业是研究地质学,其实地质学不仅是一个职业的背景,而是张炜想由此把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地理与现代中国剧烈动荡的历史构成一种关系,同时也与宁伽的自我反思构成一种对话。这使小说有了一种广阔的视野,一种苍茫悠远的背景,小说叙述空间因此显得独特。
其四,通透。对“50年代生人”及其父辈的审视。这部小说不止是反思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反思父辈的历史,而且尖锐地反映了当代社会现实纠结的精神困境。当然,它同时又以内省的笔调去写出“我们”的历史,写出“50年代生人”的命运。小说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敏锐而透彻,对这一代人的书写真挚而深切,他能够客观平静地审视一代人,揭示这代人的独特性,反思、批判与同情融为一体,有一种通透之感,留下一代人饱满的精神传记。
其五,亲切。自我的经验与细节。张炜算是中国当代少数浪漫主义特征比较鲜明的作家。在张炜的叙说中自我的经验非常丰富,带着思辨色彩,与客观化的叙述相比,他的叙述总是带着诚挚的温暖,如同与朋友握手谈心,那种亲切和诚恳溢于言表。他的批判性经常激烈而痛切,但能让人感到他对正义与善的不懈追求。因为那种亲切感,在含量如此丰伟的叙事中,同时有非常细致和微妙的感受随时涌溢而出。那些当下的细节刻画得栩栩如生,这才是小说在艺术上饱满充实的根基。那些激越的情感表达并不空洞,而是有着扎扎实实的生活质感,那些具体的描写与自我当下的感受总是被结合得相当精当。在叙述与朋友的交往时,他对友情的思考,总是与对同代人的敏锐而亲切的注视相关。
张炜立于汉语文学悠久的文学传统之上,才有如此强大的自信,才有勇气倾尽20多年的心血构造鸿篇巨制。《你在高原》融古今于一体,汇中西于通篇,从这里可以看到张炜20年的工夫,在小说叙述艺术方面,已经磨砺出自己的风格,也把汉语小说艺术推到一个新的境地,激发了汉语文学很多新的素质。它证明了中国作家的文学创造能力,也必然会证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天行者》:别样动人的教育诗
於可训
上世纪90年代,有一部改编自同名中篇小说、名叫《凤凰琴》的电影,曾让无数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也让更多人得以了解在中国广大乡村,尤其是在贫困山村,有这么一群知识分子,默默坚守在启蒙教育、为国育才的神圣岗位,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数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双肩,扛起了新中国教育的大梁,用自己的双手,夯实了新中国教育的基础。用刘醒龙的话说,他们是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凤凰琴》就是献给这些英雄的赞歌。
长篇小说《天行者》不但反映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乡村民办教育的艰难历程,表达了作者对乡村教育问题的深沉忧患和痛切思考,在反映乡村教育艰难曲折的历史、表现乡村教师矢志坚守、默默奉献的同时,也写出了生活的诗意、理想的亮色和人性的光辉。
中国现代教育起步较晚,旧式的启蒙教育,或曰基础教育,是以乡村私塾为主体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力未强,基础薄弱,在旧式私塾教育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学校教育,逐步对旧的教育模式加以改造,由私家供养到集体办学、民间办学(“民办”),才有了民办教育这种特殊的乡村教育形式。这种乡村教育形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直到上个世纪末民办教师逐步“转正”,义务教育制度推行,民办教育体制改革,近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起起落落、分分聚聚的艰难发展历程。《天行者》虽然不是历时性地全程介入当代中国的乡村教育史,但从它切入的这一时段看,却是当代中国乡村民办教育经历新旧转变、改革阵痛、社会震荡的关键时期。由在旧的轨道上惯性运行,步履维艰,到逐步引起关注,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援,乃至最终纳入农村教育改革和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迎来了一个可以预期的光明发展前景,这一切,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都得到了曲尽其致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作品中的界岭小学是当代中国乡村民办教育的历史缩影和乡村民办教育改革的微缩景观,毫不为过。
教育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立人”的问题。鲁迅当年曾把这个问题提到一个民族生存竞争的高度:“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就一个社会而言,如果连教育者的个性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精神人格得不到自由的张扬,人生价值得不到自由的实现,甚至为各种现实的条件所束缚、压抑和扭曲,很难想象他会有一种健全的人格和心智,去教育培养出一些真正在精神上自强自立的国民来。长期以来,当代中国乡村教育的最大失误,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轻慢和忽视。作品有一个中心情节,是民办教师“转正”问题。围绕这个中心情节,作者有许多让人心酸欲泪又忍俊不禁、备感荒谬的描写:一位长期瘫痪在床的民办教师,得到大家让出来的惟一一个转正指标,正襟净手,“颤颤悠悠”地填写表格,却在这庄严的一刻溘然长逝;一个年轻的民办教师,因为一念之差,利用手中掌握公章的便利,私填了转正表格,将同样是惟一的一个转正名额据为己有,结果不但没有遭到其他老师的谴责,反而顺水推舟成全了他的好事。原因之一是老师们怕毁了年轻人的前程,原因之二则是他如果不占用这个转正名额,其他老师谁也不会一个人先于他人转正,结果反而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最后,所有老师终于盼来了一次性全部转正的上级决定,但按文件规定,转正要有一定的从事民办教育的工龄,而这工龄,却要他们自己花钱去买回来,这又不免要让他们愁肠百结,求告无门。作者的这些描写,显然不是为了刻意煽情,也不纯粹是为了暴露问题,揭示矛盾,而是寄寓了他对中国乡村教育问题的深沉忧患和痛切思考。用转正来体现一个人的价值,本来就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情。尤其是对那些长期从事乡村民办教育,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乡村民办教师来说,更属荒诞不经。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荒诞不经的问题,却成了决定广大乡村民办教师的命运,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甚至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的“比生命还重要”的瓶颈问题。作者之所以把这个问题做了整个作品的情节主线,我以为,其深意就在于,他把“立人”的问题,即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问题,提到了发展乡村教育,也是振兴整个教育事业的首要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天行者》的这一立意,无疑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中国教育的积弊,也是一剂有力的针砭。
界岭小学每天用笛子奏国歌升降国旗的诗意场面,反复出现在《天行者》之中。我认为,这场面不仅昭示了一种崇高理想和爱国主义,同时还有别样的象征意味。用这种朴素的、原始的、简陋的方式,实现对神圣、崇高事物的礼敬和追求,难道不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师,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献身神圣、崇高的乡村教育事业的精神写照吗?如果要从《天行者》中寻找诗意,这诗意不是界岭的青山绿水,也不是学生的诗歌爱好,而是在界岭小学这“困厄之地”传出的“弦歌不绝”的精神。
《蛙》:文学与生命的思想难题
贺绍俊
在当代作家中,莫言无疑是一位风格独特且鲜明的作家,他写小说仿佛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王国里纵情狂欢,他的叙述是如此的汪洋恣肆,他的想象是如此的诡异奇特。但《蛙》大大减弱了莫言的风格特征,喜欢莫言风格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这部作品不是莫言最好的,他们会举出《红高粱》《檀香刑》等等,认为最该获奖的应该是这些风格鲜明的作品。我也非常喜欢这些特别“莫言化”的作品,但我同时也对莫言以另外一种姿态来写作感到了惊喜。相比于以前的写作,《蛙》显然是一部结构更为新颖、构思也非常缜密的小说。在我看来,这些变化对于莫言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莫言在《蛙》这部小说中由以往激情的莫言转化为思想的莫言。
事实上,这是一个最适合莫言发挥特长的写作素材。据莫言自己说,他的姑姑是新中国第一批接生员,几十年来在农村做妇科医生,从接生到抓计划生育,她的经历既曲折又传奇。比小品《超生游击队》更加荒诞或更加残忍、更加令人捧腹或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莫言要在这个基础上挥洒想象力太轻而易举了。但莫言的这部小说却写了7年。为什么写得这么艰难?因为一直有一个思想的石头压在莫言的内心,这使他的写作变得沉重起来。这个思想的石头莫言在小说的一开头就抛了出来。小说一开头是作家蝌蚪(不妨将蝌蚪就视为莫言本人)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先生的第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莫言告诉读者,杉谷义人先生曾在他的故乡作了题为《文学与生命》的长篇报告。“文学与生命”与其说是一个日本作家的报告题目,不如说是莫言一直萦绕在心的思想难题。
文学与生命的确是一个宏大的题目,也是古今中外的作家共同的题目。文学首先就是一种生命的书写。莫言是一位生命意识极强的作家,他汪洋恣肆的风格又何曾不是他内在生命力的下意识狂欢,那些活生生的生命体在他的遣使下恣意地活着,慷慨地死去。文学同时也是凝视生命的一种方式。作家通过文学去叩问生命的奥秘,捍卫生命的尊严,张扬生命的价值。以此看来,莫言过去主要是把“生命的书写”放在第一位,因此他的叙述充满了激情。而在《蛙》的写作过程中,莫言悄悄地将“凝视生命”放在了第一位,理性和反思成为了叙述中的主要角色。于是他面对乡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各种奇异的故事时,收敛起他的汪洋恣肆,以一种谨严和深沉的姿态,去叩问故事背后因文化、传统、伦理、政治、权力、金钱等种种因素而构成的玄机,批判了在中国充满悖论的现代化进程中顽固的国民性痼疾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悲剧宿命化的延续性。
《蛙》是由一位乡村妇科医生的引领,巡视了当代农村的生育史。生育自然关乎生命。莫言通过姑姑的故事,对深受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影响的乡村生命意识进行了全方位的表现。莫言所写的乡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习俗,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于是我们遇到的都是一些叫陈鼻、陈耳、王肝、王胆的人物。这个习俗尽管只是出自莫言的想象,但这一想象恰好是抓住了乡村传统的生命意识的关键。乡村传统的生命意识是建立在彻底物化的基础之上的,关注生命也就是在关注物质。陈鼻一家费尽心机要保住王胆腹中的胎儿,并非期待一个新的生命,因此当王胆在木筏中产下一个女婴时,陈鼻不是喜悦而是痛苦地发出“天绝我也”的哀号。姑姑此刻骂陈鼻“你这个畜生”,她所责骂的是人们的生命意识中严重的欠缺。在传统的生命意识中,最稀缺的就是对于生命质量的关注。这是乡村长年累月的艰难生存环境所决定了的。能活下来就是万幸,哪能去追求生命的质量。当人们不关注生命的质量时,生命的尊严、生命的关爱、生命的精神价值等等都变成了一种奢侈。
莫言在这部小说中强调了结构的重要性。莫言说他最终选取了书信体的形式,通过给一位日本作家的5封书信,来讲述姑姑的故事。其实这部小说算不得严格的书信体。也许只有每一部前面以楷体出现的数百字才算得上是一封书信,而后面讲故事的部分只能说是一种“伪”书信,它更像是莫言为自己设置的一道樊篱,以免在故事情节的牵引下信马由缰。但更重要的是,莫言通过对书信体的仿制就很自然地将自我摆了进去,莫言在讲述姑姑忏悔的故事时贯穿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救赎的意识,因此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莫言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对知识分子立场的追问。至于第5部的“九幕话剧”,我以为是莫言在讲述完故事后仍有思想表达的欲望,这个话剧的确也深化了关于生命质量的思考。话剧文体的嵌入或许还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莫言越来越在意语言的功力。话剧无疑是磨炼语言的文体。文学最高的境界是语言的境界。《蛙》或许可以说是莫言更加成熟的标志。
《推拿》:黑暗中的阳光
汪 政
如果从题材或故事层面看,《推拿》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盲人的作品。只不过这个故事并没有被作家演绎成想象中的同情、关怀、悲悯等人道主义主题。它去除了健全人天然的优越,而将视点全部聚焦在盲人本身。
不过,作品的意义显然不止于此。说到底,这是一部直面当下社会问题的小说,是对当下的文化追问。毕飞宇此前的长篇,如《上海往事》《平原》等,都是面对过去或面对历史的,这次他直接面对了当下眼前。毕飞宇对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世情有许多的思考,他说,一个作家如果不能以文学的方式处理现实问题不能说是最后的成功。所以,《平原》之后,毕飞宇调整了写作的姿态,《推拿》,包括他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几乎都是现实题材的作品,而且表现出非常浓厚的问题意识。
[次页标题= 导航短标题=]
《推拿》是一部有关尊严的作品。它以正面的方式书写了人的尊严,歌颂了人性的光辉。不能不佩服作家对盲人群体的了解,使他在表达尊严时找到了最直接也最具承载力的意义载体,因为“盲人的自尊心是骇人的”,他们“要比健全人背负过多的尊严”。这一特殊群体虽然生活在黑暗中,但不管面对什么,无论是生计、金钱、爱情还是生命,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尊严。金嫣为什么对一场婚礼那么向往?因为在她看来,只有那样的仪式才能见证爱情的尊严。都红的手受伤了,这对一个推拿师来说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但是她不需要怜悯,不需要施舍,更不能容忍有人出面为她的下半辈子募捐,这样的募捐在扶弱济危的名义下胁迫了多少人的意志呢?这些都是对她自尊的极大伤害。王大夫自残的情节是小说的高潮之一,残疾的哥哥要用自己的血汗钱去为身体健全的弟弟还赌债,心中的不平自然可以理解,更重要的是,这血汗钱一还他就一贫如洗了,就得去要饭,如果这样,他就要失去自己的脸面,而他是如此地“爱自己的脸”,如此地“拿自己当人”,于是,他只能对自己举起菜刀,只能用血来还债!然而,这样的方式又让他觉得自己与一个流氓没了区别,满身是血的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十足地痞,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渣。太龌龊了。他王大夫再也不是一个‘体面’的人了”。这样的自尊确实到了苛刻的地步。在作品中,我们当然可以看到他们的心计,他们的欲望,他们阴暗的另一面,比如小马与小孔的故事,沙复明与张宗祺两个老板间的角力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保持外在的磊落,都会通过正当的途径与方式,都会或勒马于悬崖,或补救于事后,这个黑暗的世界从来就不缺少光明,而这光明正来自于每个人都拥有尊严的太阳。
尊严在当前是不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尊严是不是解决当下人精神困境、构建当下人文环境的关键?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但不可否认,毕飞宇确实抓住了我们社会的文化症候之一,我们太重视结果了,太看重财富了,太放纵欲望了,太依赖物质了,为了这些,我们可以不择手段。不可否认,在当下社会,个体的人,以及具有人格特征的主体,可以说尊严普遍缺失,主体间既不尊重对方的权利,也不尊重自我的权利。侵犯尊严与自尊的丧失成为主体间关系的双胞胎。随着尊严与自尊的丧失,一系列的社会、人性、道德、伦理与文化问题成为其继发的灾难。这样的局面实际上为作家的文学批判提供了靶子,但是,毕飞宇从忧患出发,从批判出发,选择的方式却是正面的。也许,毕飞宇是要与流行的批判保持距离。
一个社会永远不可能缺少批判,但如果一个社会只有批判这样一种动作,那可能也是一种畸形甚至灾难,怀疑、质难、批判,如果缺乏理性的规约,如果总是弥漫着非理性的愤怒,它所酿成的社会情绪就会遮蔽、甚至伤害许多善良与美好的事物。大概谁都不会想到,现如今,本来与勇气和孤独为伴的批判会成为哗众取宠的媚俗。以文学而言,我们正在丧失正面书写的能力。也许,人们早已忘记了古典时代的写作经验,即从写作的难度上说,描写苦难与愤怒固然不易,但歌颂正面、传达美好更难。古人说,穷苦之辞易好,而欢愉之辞难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长篇小说写作的角度看,《推拿》所提供的经验将会慢慢显现出来,它呈现出的是一种新的长篇气质,一种与当今生活同步的美学形式,一种与传统拉开距离的现代步伐。从传统看,长篇小说与历史有着割不断的渊源,它的结构、时间、人物命运与故事的支持实际上都是由外部世界提供的,甚至直接是由外部的历史事件构成的。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而言,史诗是作家们的梦想,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一直是小说家们追逐的题材和结构小说的要素,以至于形成了叙事的模式化。当外部世界不能为我们提供戏剧性的事件时,我们的故事从哪里来?看看欧美,包括近年来与我们交流甚多的日本、韩国的小说创作,我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已经完成了这种小说现代化的转型,完成了小说与现实生活的同步化。其实,中国的许多小说家特别是年轻的小说家们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创作,但或许是未能提供较为成功的文本,更重要是因为传统长篇小说美学的歧视,这样的创作一直没有进入主流。《推拿》的出现提供了使这一新的小说美学站到前台的机会。作品以人物来划分章节,以时间为经,以人物的命运为纬,织成了一个立体的小说世界。它挣脱了传统长篇之“重”,同时又躲开了时尚小说之“轻”。这样的写作终会使长篇加入到当下思想者的行列,成为真正的时代之音。
《一句顶一万句》:跋涉人心与历史间距的精神旅程
陈福民
对于《一句顶一万句》,可说的话已经无多。这倒不是因为此前有关这部小说的议论穷尽了它的旨蕴,以至于再来发议论显得饶舌而多余,而是因为,我向来坚持一个偏激的观念:一部好的小说不适合也不可能被复述,它只能是被用心去阅读的。凡能够被简明归结出若干要点、或者是被简化意旨为“写的是某某”的那些小说,大约都未见高明。众所周知,语言是个极其平常又极为奥妙的东西,其于文学,正有“妙处难与君说”的神奇。一如刘震云在小说中反复提及的,它能“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生活日常中的悲剧性烦恼,在小说中却正是需要咀嚼会心的去处。孤独与交往、封闭与打开、执守与游离、空旷的荒芜与隔绝、失魂落魄的奔走与寻找……循环往复,余音绕梁,叙述着人心与历史的无限间距以及吴摩西们对此种间距的无限的克服。这是《一句顶一万句》对于汉语文学无可替代的贡献。小说家苦心孤诣写就一部小说,其好坏优劣的标准虽然能在理论上加以逻辑推论然后予以认定,但实际上历来无法定于一尊,至少是各有取舍各有所议。《一句顶一万句》如此,关于它的说法,也只能是如此。
说与听的烦恼
这是一部关于“说话”和“倾听”之书,同时,它更是一部虚与实永远错置的人类寓言。在这个向度上,刘震云不动声色地展开着他的人性挖掘与化腐朽为神奇的哲学沉思。
无法知道刘震云何以选择“一句顶一万句”做这部小说的名字。尽管我一直认为这个名字过于理念和粗糙,与小说那种洗练、生动、绵密、地道的语调风格颇有抵牾之处,但很显然,这个来自于四五十年前、携带着历史记忆的格言警句带给作者特别深刻的印象,用在这里,倒也是格外地恰切扣题。从“一句”开始以至书中林林总总的“一万句”,小说中的人物们,如同中了魔咒一般,纷纷掉进了“说得着”与“说不上”的陷阱。他们总是喋喋不休或者沉默寡言,但命中注定总是词不达意,总是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
卖豆腐的老杨与赶大车的老马,因为“话上被他拿住了”,两人便形成了一种奇特而脆弱的友谊,但这“友谊”最终被证明是一种蔑视与伤害;天主教牧师老詹一生致力于“主的事业”,然而终其一生,不但没有赢得一个真正的倾听者,连他的开封上级也抛弃了他;吴摩西与吴香香、曹青娥与牛书道,牛爱国与庞丽娜,牛爱国与章楚红,剃头老裴、杀猪老曾,以及书中无数面目不清的某某们,他们由渴求“说得着”始,至“说不上”终,统统活在一种莫名所以怒气冲冲的恶意中。每览书至此,总令人想起“在语言的家园中”“诗意的栖居”这类无限美好煽情之昏话,始知语言这东西,实在未可一概而论。亦如“南橘北枳”的品性,也是要看人下菜碟的。
逃离与建构
《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中国底层社会的历史,更是一部世道人心之书。
刘震云是个对无名的民间底层社会和现代中国历史情有独钟的作家,这方面,他的深刻体会与精湛心得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从《故乡天下黄花》开始,刘震云就汲汲于梳理这段悲喜交集混乱不堪的日子,迄今整整20年了。虽然其间也有《一腔废话》这类真正的废话之作,表明他的厌倦导致了严重的“逃离”倾向,但《一句顶一万句》再次证明他命中注定要对这段日子穷追不舍。《一句顶一万句》是一次在“逃离”与“建构”的悖反中重新发现并书写历史的自我救赎。
支撑起这个历史书写的根本方式,不再是之前流行的表层颠覆或者黔驴技穷的“重写”把戏。有关中国“现代性”基本元素和展开方式,普通的历史叙述教给我们的东西,已经足够我们应付普通的说法。而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独具只眼,以真正属于他自己的艺术敏感,激活了从不为人瞩目、却又实实在在支配着历史走向的民间生活。这段生活或曰这段日子,曾被认为是“卑之无甚高论”的颓唐妥协,但在事实上,没有这段生活,中国现代史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刘震云逃离了耳熟能详的“宏大叙事”,他也无意以自己的发现全盘接管历史。但就《一句顶一万句》的叙述效果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刘震云认为书中那种生活那段日子,不仅是中国现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决定性的历史因素之一。
从“呐喊”到“喊丧”
曾经无声的中国,因为有了鲁迅的《呐喊》而生出希望。但历史的吊诡却让爱讲话的小韩县长成了一个空头演说家,甚至还不如杨百顺或吴摩西的“喊丧”来得更有实际意义。把刘震云与鲁迅联系起来可能是招人厌烦的,但我始终记着罗曼·罗兰对阿Q的评价:“令人难忘的忧愁的面容”(大意)。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非常强调从杨百顺到牛爱国等各个人物的“心事”以及老詹所说的“忧烦”,他们无一不是茫然失措和心事重重的,这构成了一副忧愁麻木的人物群像。而这麻木忧愁,又往往归于无言与寂灭。如果让我定位小说的整体叙述格调,我仍然要说:“悲凉之雾遍披华林”。《一句顶一万句》固然有着刘震云一贯的黑色幽默与表面轻松的自我解构,但他在写到老裴救下杨百顺、老詹不得要领却无怨无悔传教布道、吴摩西抚养巧玲、老尤贩卖巧玲之前瞬间的不忍等等,始终怀有通透温暖的悲悯之心。即以情爱性爱论,当吴摩西看到私奔的吴香香和她的相好相濡以沫时,当牛爱国以自己与章楚红的体验回看庞丽娜与小蒋、老尚的关系时,突然就有了一种从不具备的理解力。在这种时候,哪怕是半截子的善良,也是根本性的改变。
于是,从“呐喊”到“喊丧”再到理解力的过程,其实正是人心与历史的无限间距被克服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是漫长而艰难的,但刘震云没有放弃。他固然做不成鲁迅,但他的文学写作,在满篇“过日子”的掩盖下,始终行进在一种不事张扬的精神苦旅上。
(转载自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