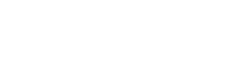记者: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部获奖作品《这边风景》。这部您39岁时在新疆开始创作的作品,却于79岁时才出版,按照您自己的说法,“好比是79岁的王蒙看到39岁的王蒙”。
王蒙:20世纪60年代,在我处于逆境的时候,我下决心到边疆去,到农村去,破釜沉舟,重新打造一个更宽阔也更坚实的写作人,打造一个焕然一新的工农化的写作人。按当时的认识,我必须写工农兵,只有写工农兵才有出路。就像我在1963年底坐着火车带着全家从北京到新疆时所吟咏的:“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志弥坚。春光唱彻方无恨,犹有微躯献塞边。”
我到了伊犁州伊宁县,巴彦岱人民公社,与维吾尔族农民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曾担任二大队副大队长。
我很快与农民打成一片,讲维吾尔语,读维吾尔文书籍,背诵维吾尔文毛主席语录与“老三篇”。我住在老农阿卜都热合满·奴尔与黑力其汗·乌斯曼夫妇家。我住的一间小屋,在我到来以后,燕子飞来做了巢,每天我与呢喃的燕子一起生活,农民们从这一点上认定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爱生活,我爱人民,我爱不同的环境与新鲜的经验,我爱雪山与大漠,湖泊与草原,绿洲与戈壁滩。我得到了爱的回报。当地的农民喜欢我。
你可以说我是在特殊处境下做出的不一般的选择,但是我选择了,我做到了,我仍然充满生机,爱恋着边疆的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一切:伊犁河、大湟渠、砍土镘、水磨,还有情歌《黑黑的眼睛》;尤其是各有特色的族群:汉、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锡伯、俄罗斯;还有馕饼、拉条子、哈密瓜与苹果园。我曾经说我在新疆16年,完成着维吾尔语“博士后”的学业。我至今回想起这一切,更要强调说,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困境中,是那里的人民保护了我。
于是有了《这边风景》,我确实书写了大量的有特色的生活细节。劳动、夏收、割草、扬场、赶车……我写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奋斗、挫折、懒汉、积极分子;我写了边疆历史的风风雨雨、恩怨情仇,我写了那里大异其趣的衣食住行婚嫁。讨论作品的时候,有学者说他们看到了西域的清明上河图,有的说边疆生活细节排山倒海。一位维吾尔族女教授说:作家把他的心交给了我们,新疆各族人民也就愿意把心交给他。
记者:请谈谈获奖后的感受。
王蒙:此书的得奖最让我感谢的是它将有利于人们关注新疆,了解新疆,热爱新疆,走近新疆。我为新疆的兄弟姐妹们高兴。
这本书的得奖,还让我相信,真正的文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41年前动笔写的书,37年前基本定稿,两年前出版,现在受到了关注。毋庸置疑,写作的年代与当下区别很大,写作时有各种的局限性,可以说当时的写作是戴着镣铐的舞蹈。然而,只要下了苦功,有了刻骨铭心的生活经验,有了血肉相连的感情交融,有了亲近大地的匍匐与谛听,有了对于人民音容笑貌的细腻记忆与欣赏,你写出来的人、生活、情感,就能突破局限、摆脱镣铐、充满真情、充满趣味,成就你所难以预见的阅读的厚味与快乐。
仍然是王蒙写的,仍然热爱,仍然多情,仍然兴致盎然,仍然一片光明,仍然有“青春万岁”的信念,有“新来的年轻人”的眼光与好奇心,有对于生活的缤纷期待,有对于爱情的讴歌,有对于历史和时代的钻研,有对于日子的珍惜与温习。
记者:在您看来,文学评奖与文学是什么关系?
王蒙:茅盾文学奖的获得当然令人高兴。文学奖引人注目,因为它向读者推荐了文学。奖为文学增光,前提是文学能不能给奖增光,能不能给予心灵以抚摸与冲击、营养与激扬。只有文学本身可爱,奖才可爱。离开了作品去研究文学奖,未免可笑与可悲。奖能锦上添花,奖能促进发行,但是奖不能弥补缺陷,奖不能化东施为西施。把功夫放在争取得奖而不是写好作品上,只能说是作者没出息到了极致。(本报记者 饶 翔)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