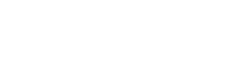陈来 李存山
一个民族要独立、要生存、要发展,必然要对自身独属的民族精神加以发现、反思和重建。透过历史观察近代文化,民族精神已然成为一个普遍的命题。精神作为客体存在,必须要为其寻求并确立民族主体性。相较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文化对主体性的强调尚没有如此突出,因此就要对此有所转变。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奠基人,张岱年先生以一种超脱性的态度提出针对民族的成功要实现个人主体性和民族主体性的结合,在文化之相上真正思考文化之体。在这一要求下,必须对群体性的民族精神提出正名,强调民族主体性,树立文化自觉意识。
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什么?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没有中断,一定有其内在动力和内在精神,张岱年先生明确将这一文化精神所指指向“刚健有为,厚德载物”,这种中华精神蕴含了一种文化力量。《中国文化精神》即是对张岱年先生这种精神力量的内在理解和一贯见解的表述。

思辨审慎——文化精神的理性认知
对待文化剖析,张岱年先生始终持辩证分析的方法态度,唯有用对比法、辩证法才能对中国文化精神进行理性认知,才能既有鉴于文化之整,又有鉴于文化之分,新的文化是可以对它进行分析择取的,是可以进行吸取的,有整有分;才有鉴于文化之长和文化之变,文化有它的发展性、继续性,变即文化发展的继续性,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才能既有鉴于文化之同,也有鉴于文化之异,“同”即文化的普遍性,世界文化存在相同之处,“异”则暗含着文化有其民族性。如果当今的民众能够对以上的理念深刻理解,那么在认知中国文化精神的方向上就不会有所偏颇。

《中国文化精神》张岱年 程宜山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审慎分析、解析解构的方法贯穿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始终。张岱年先生在论述每个细节问题时,对于简单化、主观化的分析倾向都是完全拒斥的。这种对中国文化理性分析的态度,使得张先生能够居于一个较高的据点上全面地看待中国文化精神的得失。《中国文化精神》这部著作在肯定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客观存在的同时,在提出对民族精神传承和弘扬的要求下,同时要求对这一精神进行创造性综合。早在40年代,张岱年先生曾在《文化通全》这篇论文中提出文化的五要素:“正德、利用、厚生、立制,致知”,这对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核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和意义,同时以审慎分析的方法,百家争鸣,综合创新。《中国文化精神》完稿至80年代,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文化经历过90年代的国学热,也历经了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客体状态,在民族自信增强,民众思想认识发展的基础上,这本著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作为文化史来读,探究其中深刻的见解,也可作为严谨的哲学读物来看,分析其所论述的观点和论证。
积习治病——民族本性的再发现
近代文学从五四以后到30年代有一个基调,即对国民性的批判。五四时期对国民性的批判被重新提及。作为一种文化反思,这种批判的主导意义仍是积极的,因为民族要前进,民众需要反思缺点。因此,我们说对国民性的批判、反思有其迫切性,但是张岱年先生认为这一基调从概念上来讲不科学,他提出“积习治病”,当下所谓的国民性其实不是国民性,只是国民积习,是习惯,不是本性,中华民族的本性,有可能会迷失,但仍然可以自觉的认知。所谓国民性,是可以改变的,民族本性则不同,只要民族文化还在,民族性永远不能改变。无疑,这一观点是反潮流的。所谓的文化热、国学热现象,比较流行的仅仅集中在较为肤浅的国民性批判。诚然,必须承认对于中国文化的这一认识有一种点醒作用。但是提出之后并没有被民众所深刻反思,很多人尚且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文化精神》在今天这种文化背景下,将这个问题重新讲出来,虽然今天坚决或者全面反对中国文化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从理论上回溯这个问题还是有意义的。
综合创新——中国文化精神的走向
凡事有破必有立,所以张岱年先生在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得失进行反思性论述之后,提出其走向应该是综合创新。所谓综合创新,就是要综合中西文化之优长,创造出一种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新的文化。张岱年先生的文化观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他其实是运用对比法、辩证法针对全盘西化和全盘反传统进行思辨性论述。因为全盘西化和全盘反传统倾向都是形而上学,都不是辩证法。针对这种文化观,张岱年先生讲了文化系统和文化的元素、要素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讲可离与不可离,相容与不相容。有些人说为什么要全盘西化,因为只学习西方其中一点是学不来的,要全盘都划过来才可以学到,还有为什么要全盘反传统,我们中国文化有一点不好的,光把这个择出去不行,因为它都是紧密系统里不可离的。但张岱年先生认为并非如此,首先是可离与不可离,文化的要素有些是不可离的,有些是可离的,一个文化要素跟它的文化体系的关系是复杂的,有些是可以离开的,可以结合到另一个系统,这是张岱年先生的一个重要观点。其次是相容与不相容,一个文化领域是复杂的,不见得全都顺着一个方向,有些东西是看似相反,其实是相承的、相容的,看起来不相容,实际上文化整体上还是相容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法家之间看起来非常对立,但是在中国文化体系的历史发展中,仍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其相容性。总之,张岱年先生认为学习西方不见得要全盘西化,西方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拿过来结合在我们文化里面,不需要整体地把西方文化全部移植过来。
关于文化结构和文化要素之间还有一个讲法,中国文化不能全盘否决,因此就要从结构方面入手,把旧的结构消减,而不是抛弃所有元素。所以张岱年先生既注意结构,又注意要素和系统的关系、要素和要素的关系,这一讨论在本书中十分深入。在这一意义上,张岱年先生在文化理论上的研究,在一些概念上、方法上的分析是比较细微深刻的,在今天重新拿出来探讨很有意义。
有关张岱年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精神》这本书中窥探一二。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张岱年先生阐述的根基,他将中和作为中国人的基本价值态度,以中庸的思维方式将民族精神高度概括为厚德载物,引领民众本着实事求是、辩证分析的方法逐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所以张岱年先生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值得大家去重视、去把握。
——摘自《光明日报》